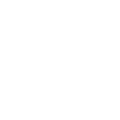昏黄的光线,勉强涂抹在牢房的每一个角落,却无法驱散墙角那些大片大片的、顽固的阴影。
汗臭、脚臭、没冲干净的尿骚味,混合着每周喷洒一次的、刺鼻的消毒水气味,构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、名为“监狱”的嗅觉符号。
墙壁摸上去是冰冷而潮湿的,指尖能感觉到一层滑腻的、看不见的霉菌。
高墙上那扇小窗外,是江州连绵不绝的冬雨,天空永远是铅灰色的。
肖文蜷缩在下铺最靠墙的角落,用那床散发着霉味的、又薄又硬的被子,将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。
像一只把自己藏进壳里的蜗牛。
这是他唯一能拥有的、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一个长两米、宽一米的洞穴。
在这个洞穴里,他可以假装自己不存在。
“喂,那个新来的书呆子,又装死呢?”
“别管他了,妈的,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,晦气。”
“听说是个强奸犯?啧啧,看着文文弱弱的,没想到还好这口。”
“是猥亵,强奸哪能判这么点。”
”猥亵能判两年半啊?扯鸡巴淡呢。“
隔壁床铺的囚犯在打牌,污言秽语和香烟的劣质气味一起飘过来。
肖文把头埋得更深了。
他将耳朵紧紧贴在冰冷的墙壁上,试图用墙体的冰冷,来压过那些钻进耳朵里的声音。
(听不见……我什么都听不见……)
他不是在自欺欺人。
他是真的,在努力让自己“听不见”。
就像他努力让自己“感觉不到”一样。
感觉不到冷,感觉不到饿,感觉不到疼。
只要不去看,不去听,不去想,痛苦就不会存在。
这是他入狱一个月以来,学会的唯一生存技能。
铁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,被打开了。
“2357号,出来!有律师见你!”
狱警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锯子。
牢房里瞬间安静下来,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肖文的床铺。
肖文的身体僵硬了。
律师……
是那个法院指派的,没什么干劲的公共律师。
他来做什么?
哦,对了,上诉期快到了。
他慢吞吞地从被子里钻出来,将囚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。
一个月的时间,他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,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。
他没有看任何人,低着头,跟在狱警身后,走过长长的、回音不断地走廊。
会见室里,公共律师一脸疲惫地坐在桌子对面。
公共律师: 「肖文,考虑得怎么样了?明天就是上诉期的最后一天了。你要是决定上诉,我今天就得把材料交上去。」
(上诉……)
这个词,像一根针,扎了一下他那颗已经快要停止跳动的心脏。
他的脑海里,瞬间闪回了法庭上的画面。
周海仪那轻蔑的眼神。
苏媛那梨花带雨的脸。
旁听席上那些鄙夷的目光。
还有自己那句“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”,通过音响,在整个法庭里回荡。
再一次……
要再一次经历那种被公开处刑的羞辱吗?
要再一次,站在那个女人面前,听她用那些悲悯的词汇,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吗?
(不……不要……)
恐惧从他的胃里升起,让他想呕吐。
他害怕。
他怕得要死。
他宁愿在这里烂掉,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。
「喂?说话啊。你到底上诉还是不上诉?」
肖文张了张嘴,喉咙里却像是被什么给堵住了。
他想说“我放弃”,但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。
他只能沉默。
用沉默,来做出回答。
公共律师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,不耐烦地叹了口气。
「行了行了,我知道了。你不说话,我就当你默认放弃了啊。」
「也是,这种案子,证据确凿,还是周法官判的,上诉也是白搭。」
他草草地在文件上签了个字,收拾好东西,站起身就准备走。
在走到门口时,他像是想起了什么,回头说了一句。
「哦,对了,你家里人让我给你带了信,待会儿管教会拿给你。」
家。
信。
这两个字,让肖文死灰般的眼睛里,终于泛起了一丝微弱的光。
(如果他们能亲自来就好了。)
(别想那么多,可能是太忙了吧。)
回到牢房,他果然拿到了信。
信封上是母亲熟悉的字迹。
他躲回自己的“洞穴”,用颤抖的手,借着昏黄的灯光,展开信纸。
信里,母亲用大段大段的文字,诉说着对他的思念,坚称他是被冤枉的,鼓励他一定要坚强,一定要上诉。
父亲也在信的末尾加了几句,让他好好吃饭,不要想太多。
肖"文把信纸凑到眼前,贪婪地嗅着上面残留的、来自“外面世界”的味道。
他把每一个字都读了十几遍,直到能完整地背下来。
(妈妈……爸爸……)
(对不起……我放弃上诉了……我太没用了……)
愧疚感从心底流向全身,但他顾不上了。
只要还有人相信他,就够了。
只要这个世界上,还有人把他当“肖文”,而不是“2357号”,他就还能撑下去。
之后的日子,家信成了他唯一的期盼。
第一封。
第二封。
第三封。
信里的内容,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母亲的鼓励越来越少,取而代之的,是关于家里琐事的抱怨。
“你弟弟上学要花钱……”
“邻居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……”
“你爸因为你的事,在单位也抬不起头……”
父亲不再写字了。
信纸上的暖意,一点点褪去,变得和牢房里的空气一样冰冷。
直到第五封信。
那是一张很薄的信纸,上面只有短短的一行字。
是父亲的笔迹。
“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我们也要过日子。”
“我们也要过日子。”
短短的八个字。
像八根烧红的铁钉,狠狠地钉进了肖文的眼球里。
世界,安静了。
头顶的电流声。
隔壁床的呼噜声。
窗外的雨声。
就像瞬间被按下了“静音键”,只剩下耳边一个“嗡——”的长音。
他拿着信纸的手,没有一丝颤抖。
他看着那行字,看了很久很久。
他眨了眨干涩的眼睛。
没有眼泪。
原来,人真的可以悲伤到流不出眼泪。
他抬起另一只手,捏住信纸的一角。
然后,开始撕。
嘶啦——
第一下。
嘶啦——
第二下。
他把信纸撕成细细的长条。
然后,再把长条撕成小小的方块。
一片,一片,又一片。
直到那张信纸,变成了一堆无法辨认的、雪花般的白色碎片。
他松开手。
碎片从他的指缝间簌簌落下,散落在肮脏的床单上。
像一场无声的、只为他一人而下的雪。
从那天起,2357号彻底死了。
他不再看书,不再发呆,不再去想任何事情。
每天,他按时起床,吃饭,参加强制劳动,回到牢房,睡觉。
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,精准地执行着每一个指令。
他的眼睛里,再也没有了任何光。
那颗曾经炽热、曾经不甘、曾经还抱有最后一丝幻想的心脏,被家人亲手挖了出来,扔进了江州冬天最冰冷的死水里。
现在,这里彷佛只剩下一具名为“肖文”的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