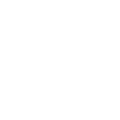18.发展贸易与汉化
返回部落后,我坐在帐篷里,对着那张盖着朱红大印的册封文书看了整整一夜。火塘里的光一跳一跳的,把那几个字映得忽明忽暗——“狼部镇守使”。旁边还摆着那份驻藏大臣衙门开出的贸易许可书,上面写着准许狼部每年一次,携带皮毛、牛羊、宝石等货物,前往西宁城互市。
我心里有事。
第二天一早,我把阿依兰叫到帐中。
她走进来的时候,阳光从帐门缝里钻进来,照在她脸上。那脸白白的,眉眼间带着凉州汉人女子的那种秀气,可那身架、那走路的姿态,又明明是狼部女人的——腰扭得软,步子踩得稳。
她站在我面前,低着头,那睫毛长长的,盖着眼睛。
“头人叫我?”
我望着她。
这个女人,是狼部几百号人里唯一一个在汉地生活过的。她嫁去过凉州,跟着那个汉人商人过了三年,男人病死后,她又回了狼部。她会说汉话,认得几个汉字,知道汉人的规矩,知道汉人怎么买卖,怎么算账,怎么说话。
这正是我要的。
“阿依兰,”我说,“从今天起,你跟着我夫人,就是神女。”
她抬起头,那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又低下去了。
“是。”
“不是跟着她伺候她,”我说,“是做她的贴身女官,教她汉地的规矩。过些日子,我们要去西宁。”
她听了,那眼睛亮了一下。
我接着说:“你去办几件事。第一,去各头人家,告诉他们,每家按人头凑皮毛,要最好的,狼皮、狐皮、貂皮,不要那种有洞的、有疤的。凑够三千张。”
“三千张?”她愣了一下。
“对。还有羊,两千头;牛,五百头;马,二百匹。宝石,一百颗。要咱们狼部山里出的那种红宝石、蓝宝石,不要那种碎的、裂的。”
她站在那里,手指头在袖子里动着,像是在算。
“头人,”她轻声说,“这数目不小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望着她,“可这是头一回。头一回办得漂亮,往后就有第二回、第三回。咱们狼部要的不是这一回的买卖,是往后几十年的路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还有,”我说,“挑人。挑二百个年轻精壮的男子,要那种见过世面的、不怯场的。他们的婆娘也带上。”
“婆娘也带上?”她又愣了一下。
“对。让那些汉人看看,”我嘴角动了动,“咱们狼部不是只会杀人的蛮子,咱们也有家,有女人,有孩子,有日子要过。”
阿依兰站在那里,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光——是那种“我明白了”的光。
“头人想得远。”她说。
我摆摆手:“去吧。”
她转身要走,我又叫住她。
“阿依兰。”
她回过头。
“你在凉州那几年,”我说,“过得怎么样?”
她愣了一下,那眼睛里闪过一点东西——很快,可我看清了。那东西是疼,是那种被埋起来的、不愿再翻出来的疼。
她低下头。
“都过去了,头人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往后,”我说,“你跟着我夫人,我不会亏待你。”
她抬起眼,望了我一下,那一眼里有很多话,可她说出来的只有两个字。
“是。”
她出去了。
帐门落下,阳光被截断,只剩火塘里的光还在跳。
接下来的日子,整个狼部都动了起来。
阿依兰这个女人,真是个能干的。她跑遍了十几个头人的帐篷,一家一家地数皮毛,一张一张地看成色。那些头人起初还拿次货糊弄她,她也不吵,只是把那皮毛往地上一扔,转身就走。第二天那头人乖乖地把好皮子送来了。
三千张皮毛,堆在部落中央的空地上,像三座小山。狼皮是灰的,狐皮是红的、白的,貂皮是黑的、棕的,堆在一起,在阳光下泛着油亮亮的光。
两千头羊,五百头牛,二百匹马,在营地外面圈了一大片,黑压压的,那叫声从早到晚不停。
一百颗宝石,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,我亲自数过。那些宝石是狼部女人从河里、从山里一粒一粒捡来的,红的像血,蓝的像天,在那袋子里一倒出来,叮叮当当的,亮得晃眼。
人也挑好了。二百个年轻精壮的男子,都是猎户出身,腰里别着刀,背上挎着弓,站在那儿像二百棵树。他们的婆娘站在旁边,有的抱着孩子,有的背着包袱,脸上有兴奋,也有怯意。
出发那天早上,太阳刚冒头。
母亲站在队伍前面,穿着阿依兰给她做的汉人衣裳——青布的褂子,黑布的裙子,头发也梳成了汉人妇人的样子,在脑后挽了个髻。她站在那里,身子绷得紧紧的,那手攥着,攥得指节都白了。
我走过去,站在她面前。
她抬眼望我,那眼睛里亮亮的,有紧张,有期待,还有那种“妈听你的”的光。
“妈,”我说,“别怕。”
她点点头,没说话。
阿依兰站在她旁边,也是一身汉人打扮,蓝布的褂子,白布的裙子,脸上薄薄地敷了粉,那眉眼更显得秀气了。她手里捧着个木盒子,盒子里装着那封镇守使任命书和贸易许可书,上面盖着大印,用绸子包着,一层一层的。
我翻身上马。
手一挥。
“走。”
队伍动了。
二百多个狼部人,赶着几千头牲口,驮着几千张皮毛,像一条长长的蛇,从山里蜿蜒出去,朝着东边,朝着西宁城的方向。
走了七天。
第七天傍晚,西宁城的城墙出现在地平线上。
那城墙是土黄色的,在夕阳里泛着红,高高的,长长的,一眼望不到头。城墙上有箭楼,有垛口,有旗子在风里飘。城门外头,是一大片平地,平地上有零零落落的帐篷,有赶路的人,有商队,有官兵在巡逻。
我勒住马,望着那座城。
这就是汉人的城。
我十多年没见过的城。
母亲骑着马,慢慢靠到我身边。她也在望那座城,那眼睛里亮亮的,有一种我说不清的光。
“儿啊,”她轻声说,“这城真大,虽然比不上穿越前的现代化都市,但在这个年代,我们终于看见一点点文明的样子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咱们进去吗?”
“进。”我说,“等明天。”
我们在城外找了块地方,扎下帐篷。那一夜,营地里烧了很多堆火,火光一闪一闪的,把那些皮毛、那些牛羊、那些人的脸都映得红红的。没人说话,都在望着那座城,望着那城墙上明明灭灭的灯火。
第二天一早,我们往城门走。
走到离城门还有三四里地的时候,远处来了一队人马。
是官兵。
我数了数,二十几骑,都穿着甲,挎着刀,为首的那个骑着一匹黑马,马上的军官三十来岁,方脸,浓眉,眼睛不大,可那眼神锐锐的,像刀子一样在我们身上刮。
他在离我们十几步的地方勒住马。
那眼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扫了一圈——扫过那些穿着皮袍的狼部男子,扫过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,扫过那些驮着皮毛的牲口。那眼神里有警惕,有打量,还有一种“这些蛮子来干什么”的疑问。
阿依兰下了马。
她捧着那个木盒子,走上前去,在离那军官几步远的地方站住。她弯了弯腰,那动作是汉人的礼,弯得不深不浅,刚刚好。
她把木盒子打开,取出那两样东西——镇守使任命书,贸易许可书。她双手捧着,举过头顶,递上去。
那军官愣了一下。
他伸手接过,低头看。
看着看着,那眉头动了动。
他抬起头,望着阿依兰,又望望我们这些人。
“狼部的?”他问。
阿依兰点头:“是。”
“狼部镇守使?这是什么地方?驻藏大臣属地的?”他又看了看那文书,“你们狼部什么时候有了镇守使?”
阿依兰正要答话,我下马了。
我走到她身边,站在那军官面前。
那军官望着我——望着我这身狼皮袍子,望着我这乱糟糟的头发,望着我这张十多年没被汉人看见过的脸。
我开口。
用汉话。
用最标准的、小时候在江南老家学的汉话。
“将军阁下。”
我故意抬高了这称呼。
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。
“鄙人就是汉人。”我说,“江南人士,祖籍苏州府吴县,我确实是江南人士,只不过不是这个时空下的人,而是一个更繁华千万倍的,真正的江南。”
他愣在那儿,那嘴微微张着。
“十多年前,”我继续瞎编说:“家父带着我去波斯做生意。路过这片地方的时候,遇了风沙,迷了路,被蛮人掠了去。”
我顿了顿。
“如今机缘巧合,已经是狼部头人。此番带着狼部重回华夏,向朝廷纳贡,与汉家互市。”
那军官站在那里,望着我,那眼睛瞪得大大的,像见了什么稀奇事。
他望了我许久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连说了几个“好”字。
“好,好,好。”他说,“本官在这西宁城外巡查了三年,头一回见着这么守规矩的蛮——不,这么守规矩的部族。”
他翻身下马,走到我面前,抱了抱拳。
那动作是汉人的礼。
我也抱了抱拳。
他看着我,那眼睛里还有惊奇,可那惊奇里有了一种东西——是敬,是那种“你这个人不容易”的敬。
“这位兄弟,”他说,“你是哪年离的江南?”
我想了想。
“绍武27年。”
他点点头,那眼睛里的光更深了。
“十三年了。”他说,“不容易。”
我没说话。
他转身,朝身后那些官兵挥了挥手。
“开路。带他们去东市。”
我们跟着那队官兵,绕过城墙,来到城东的一个大空场上。那空场四周围着木栅栏,里头搭着许多棚子,棚子里有人在卖东西,有人在买东西,有汉人,有回人,有藏人,有各种说不清哪族的蛮人,吵吵嚷嚷的。
那军官领着我们进了一个最大的棚子。
棚子里有个汉人老头,戴着瓜皮帽,留着山羊胡,坐在一张案子后面。案子上摆着笔墨纸砚,摆着算盘,摆着几本簿子。
那军官走过去,跟那老头说了几句,把那两样文书递给他看。
老头看了,点点头,从案子里拿出一个本子,翻开,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。
然后他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这位头人,”他说,“你们带来的货物,就在这棚子里卖。卖多卖少,是你们的本事。税嘛——”他指了指那文书,“朝廷有令,新归附的部族,头一回互市,免税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多谢老丈。”
老头摆摆手。
那军官走过来,拍了拍我的肩。
“兄弟,”他说,“好好卖。往后路还长。”
我望着他。
“将军贵姓?”
“姓周。”他说,“周德胜。陇西军前营哨官。”
“周哨官,”我说,“今日之恩,我记下了。”
他笑了笑,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那棚子里,望着这空荡荡的棚子,望着棚外那些来来往往的人,望着远处那高高的城墙。
阿依兰走到我身边。
“头人,”她轻声说,“咱们开始吧?”
我点点头。
“开始。”
她转身出去,招呼那些狼部人把皮毛、宝石、牛羊赶进来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这一切。
心里有一团火。
那火是——回来了。
那皮子一摆出来,就有人围上来了。
最先凑过来的是个胖子,穿着绸子褂子,手指头上戴着三个金戒指,在那阳光下一闪一闪的。他蹲在那儿,捏着一张白狐皮,翻来覆去地看,那手指头在皮毛里摸着,摸了一遍又一遍。
“这皮子,”他开口,那声音尖尖的,“哪儿来的?”阿依兰站在旁边,笑着说:“这位爷,高原上的,狼部出的。”“狼部?”那胖子抬起头,眯着眼看我,“没听说过。”我没说话。
他又低下头,继续摸那皮子。摸着摸着,那眼睛亮了。
“这毛,”他说,“这手感,这光泽——好东西。”他站起来,拍拍手,望着我。
“多少?”我伸出八个手指。
“八十两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那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,又转到那堆皮子上。
“你有多少?”“三千张。”他的嘴张开了。
三千张。
他站在那里,那脑子在飞快地转。我瞧得出来,他在算,算能不能吃下这么多,算转手能赚多少,算——“这位兄弟,”他说,“你等着。”他转身就走,走得飞快,那胖身子一颠一颠的。
不到半个时辰,那棚子里就挤满了人。
有穿绸子的,有穿布袍的,有戴瓜皮帽的,有缠头的。那口音也是五花八门的——西宁本地的,凉州来的,还有操着关中口音的,山西口音的。他们挤在那些皮子跟前,你推我,我推你,争着抢着往前面挤。
“这张是我的!”“我先看中的!”“你出多少?我出八十五!”“九十!”“一百!”那声音吵吵嚷嚷的,像一锅烧开了的水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这些人,望着这些争着抢着要买我们狼部皮子的汉人商人,心里有一团火在烧。
阿依兰挤到我身边,那脸热得红红的,全是汗。可她在那笑,那眼睛亮亮的,像两盏灯。
“头人,”她说,“八十两一张,三千张——那是二十四万两。”我点点头。
二十四万两。
这只是皮子。
还有牛羊。
牛羊的价更高。
尤其是那牛。
高原上的牛,是出了名的能驮能走。那些从关中、山西来的商人,围着那几百头牛转了一圈又一圈,那眼睛恨不得长在牛身上。
“这牛,”一个黑瘦的汉子摸着牛背,“能走多远?”“从咱们这儿,”我说,“走到拉萨,不带歇的。”他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你是狼部的?”“是。”他点点头,没再问,转过身去跟旁边的人嘀咕了几句。然后他回来,伸出两个手指。
“一头,二百两。”我摇摇头。
“三百。”他皱了皱眉。
“太高了。”我指了指那牛腿,那牛蹄子。
“你看看这蹄子,看看这腿上的肉。你这辈子见过几头这样的牛?”他低头看了看,又抬头看了看我。
然后他笑了。
“行,”他说,“三百就三百。我要一百头。”五百头牛,二百两到三百两一头,那是十几万两。
两千头羊,一头二十两,那是四万两。
二百匹马,一匹五百两,那是十万两。
还有那一百颗宝石。
那些宝石,是最后卖的。
我把那皮袋子往案子上一倒,叮叮当当的,那些红的蓝的宝石在阳光下滚了一案子,亮得晃眼,亮得那些商人的眼睛都直了。
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挤到前面,拿起一颗红的,对着阳光照。那光透过宝石,在他脸上映出一团红红的光。
他看了许久。
放下。
又拿起一颗蓝的。
再看。
再放下。
他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这位头人,”他说,“这宝石,你是论颗卖,还是论袋卖?”我望着他。
“你出什么价?”他想了想。
“这一袋,”他说,“我出五万两。”旁边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我没说话。
他又看了看那袋子里的宝石,咬了咬牙。
“六万。”我伸出手。
“成交。”那老头笑了,那笑从满脸的皱纹里溢出来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,数了数,递给我。
我接过,交给阿依兰。
阿依兰捧着那叠银票,那手在抖。
我瞧着她那抖着的手,瞧着她那亮亮的眼睛,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。
这还只是开始。
当天晚上,我把那些年轻人都叫到帐篷里。
帐篷里点着好几盏灯,照得亮堂堂的。那些年轻人站在我面前,有的十五六,有的十七八,脸上还带着白天看热闹时的兴奋。
我望着他们。
“你们今天都看见了。”我说,“看见那些汉人商人是怎么抢咱们的皮子的,看见那银子是怎么流进咱们口袋的。”他们点点头。
“可你们知道,”我说,“为什么那些商人肯出这么高的价?”他们愣了愣,互相看了看。
一个胆子大的开口:“因为咱们的皮子好。”我摇摇头。
“不只是因为这个。”他们望着我,等着。
“因为他们认咱们了。”我说,“因为他们知道咱们狼部有镇守使,有朝廷的文书,是归附了的。他们知道跟咱们做买卖,不会惹麻烦,不会被官兵抓。”我顿了顿。
“可这还不够。”他们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了问号。
我指着那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他叫阿固,是西头人的小儿子。
“阿固,”我说,“你明天去儒学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“儒学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西宁城的儒学。去念书,学汉人的字,读汉人的书,懂汉人的道理。”他的嘴张着,那脸上有茫然,有怯意。
“头人,”他说,“我——我连咱们狼部的字都不认得几个——”“那就从头学。”我说,“学费我出。你在那儿念三年,五年,十年,念到你能写会读,念到你能跟汉人秀才坐在一起谈诗论文。”他站在那里,那手攥着,攥得紧紧的。
我望着他,望着他身后那十几个差不多大的少年。
“你们也是。”我说,“都去。学费我全包。谁念得好,往后狼部的事,就有他一份。”他们站在那里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我又转向另一拨人——那些二十出头、身板结实的年轻人。
“你们,”我说,“明天去周哨官的军营。”他们愣了。
“去当兵?”“对。当兵。跟着汉人官兵一起操练,一起巡逻,一起守这西宁城。”我望着他们,望着他们那脸上的不解。
“你们以为我让你们去当兵,是为了什么?”没人说话。
“是为了让那些汉人知道,”我说,“咱们狼部的人,也能穿他们的甲,也能挎他们的刀,也能跟他们站在一起,守同一个城,护同一个地方。”我的声音沉下来。
“你们去了,好好干。别惹事,别给狼部丢脸。干好了,往后周哨官他们,就把咱们当自己人。”那几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,然后齐刷刷地点头。
“是。”他们都出去了。
帐篷里只剩我和阿依兰。
她站在那里,望着我,那眼睛亮亮的。
“头人,”她轻声说,“你想得真远。”我望着她。
“不远不行。”我说,“狼部要想活下去,要想活得好,就得融进去。融进这大夏王朝,融进这汉人的天下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那明天,”她说,“我去买那些东西——茶叶,丝绸,瓷器,铁器,种子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还有一样。”“什么?”“首饰。胭脂水粉。”她愣了一下,那嘴角动了动,像是想笑又忍住。
“给——给老夫人?”我点点头。
“还有,”我说,“给咱们部族的女人,每人都买。你挑,挑好的。”她站在那里,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
“头人,”她说,“老夫人有福气。”我没说话。
第二天,阿依兰带着人进城了。
我在营地里等着,看着那些年轻人背着包袱,一步三回头地往儒学那边走。阿固走在最前头,那背挺得直直的,可那手一直在抖。
我又看见那几个去军营的,被周哨官的人领走。周哨官拍着他们的肩,说着什么,他们点着头,那脸上有紧张,也有一种“不能丢脸”的硬气。
傍晚的时候,阿依兰回来了。
她身后跟着十几个人,赶着几辆大车。那车上装得满满的,用粗布盖着,可那布下面,隐隐约约能看见那些东西的形状。
她走到我面前,那脸上红红的,全是汗,可那眼睛亮得厉害。
“头人,”她说,“买回来了。”我掀开第一辆车的布。
下面是一袋一袋的茶叶,压得实实的,那茶香从那布袋里透出来,清清爽爽的。
第二辆车,是丝绸。一匹一匹的,叠得整整齐齐,红的绿的蓝的紫的,在那夕阳里泛着光。
第三辆车,是瓷器。碗、盘、瓶、罐,都用稻草裹着,塞得紧紧的。我拿起一个碗,对着光看,那碗薄薄的,白白的,光能透过去。
第四辆车,是铁器。锄头、镰刀、犁头、锅,黑压压的堆了一车,那铁在夕阳里泛着冷冷的光。
第五辆车,是种子。一袋一袋的,麦种、豆种、菜种,袋子上贴着红纸,写着字。
第六辆车——我掀开布。
那下面是一箱一箱的首饰,还有一盒一盒的胭脂水粉。
那首饰有金的、银的、玉的、玛瑙的,在那箱子里挤着,闪得人眼睛疼。那胭脂水粉的盒子小小的,圆的方的,红红绿绿的,摆得整整齐齐。
我抬起头,望着阿依兰。
“都买了?”她点点头。
“按头人说的,每样都买了一些。够咱们部族的女人们分几轮了。”我点点头,从车上拿起一个银镯子,又拿起一盒胭脂。
“这个,”我说,“给我妈送去。”阿依兰接过,转身要走。
我又叫住她。
“阿依兰。”她回过头。
“你自己也挑,”我说,“挑你喜欢的。算是——算是你这趟辛苦的。”她愣了一下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过。
她低下头。
“是。”她走了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那几大车东西,望着那些围过来的狼部人,望着他们那亮亮的眼睛,那笑。
可我心里,还在想着帐篷里的那个人。
想着她穿上新衣裳的样子。
想着她戴上那银镯子的样子。
想着她抹上那胭脂的样子。
我转身,往帐篷走。
帐篷里点着灯。
母亲坐在那堆皮毛上,手里捧着那银镯子,对着灯看。那银镯子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,把她那脸映得亮亮的。
她抬起头,望见我,那眼睛里的笑溢出来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你看。”她把那镯子套在手腕上,那白白的腕子衬着那银亮的镯子,好看得很。
我走过去,坐在她身边。
她又拿起那盒胭脂,打开,用指尖沾了一点,在手背上抹了抹。那胭脂红红的,在她那白白的皮肤上像一滴血。
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好看吗?”我点点头。
她笑了,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,从那嘴角溢出来。
她把那胭脂盒放下,靠在我肩上。
那身子软软的,热热的。
我伸手搂着她。
我们就这样坐着,坐了许久。
然后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软软的,像春风。
“老公——”那两个字让我心里一热。
“嗯?”“妈今天高兴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妈这辈子,没收过这样的礼。”我低下头,亲了亲她的头发。
那头发里有一股味儿,是她的味儿,是那种让我安心的味儿。
可就在这时,她的身子僵了一下。
我抬起头,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。
帐篷门掀开了。
阿依兰站在门口。
她手里捧着一个盒子,那盒子小小的,想来也是什么首饰之类的。她站在那里,望着我们——望着我搂着母亲,望着母亲靠在我肩上。
她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快得几乎看不清。
可我看见了。
母亲也看见了。
阿依兰低下头。
“老夫人,”她说,“头人让我挑首饰,我给老夫人多挑了一件。”她走进来,把那盒子放在母亲面前。
然后她退后一步,低着头。
“我先出去了。”她转身,走了。
帐篷门落下。
母亲坐在那儿,望着那门,望着那落下的帐子。
她不说话了。
我望着她。
“妈?”她没应。
我又叫了一声。
“妈?”她转过头,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的笑没了。
那眼睛里有一种东西,是我没见过的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可那轻里有沉。
“儿啊——”她又叫我儿了。
不是老公。
是儿。
“阿依兰这女人,”她说,“真能干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是能干。”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“比妈能干。”那五个字像五块石头。
我愣了一下。
“妈——”她摇摇头,不让我说下去。
她低下头,望着那盒子,望着那银镯子,望着那胭脂。
然后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有了笑——可那笑不是刚才那种笑了。那笑里有什么东西,我说不清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妈不会怪你。”我望着她。
“妈只求你一件事。”“你说。”她伸出手,摸着我的脸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热热的。
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软软的,可那轻软里有东西在颤。
“别让妈看见。”那五个字像五把刀子。
我张开嘴,想说什么。
可她用手指按住我的嘴唇。
“别说话。”她说,“别说话。”她靠进我怀里。
那身子软软的,热热的。
我把她搂住。
搂得紧紧的。
帐篷里静静的。
只有炉子里的火在噼噼啪啪地响。
我望着那跳动的火光,望着那落在我们身上的光,望着怀里这个女人——我的妈,我的女人,我的妻。
心里有一团火在烧。
那火里有热,有疼,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阿依兰的脸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快得几乎看不清。
可我看见了。
第二天一早,天刚蒙蒙亮,我就把剩下的人叫到了一块儿。
营地边上有一条小河,河水清清的,在晨光里泛着亮。那群狼部的年轻人站在河边上,有的还在揉眼睛,有的打着哈欠,有的互相推搡着,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
我站在他们面前。
阿依兰站在我旁边,手里捧着一个包袱。母亲站在不远处,靠着帐篷柱子,那眼睛在我身上,也在阿依兰身上。
“把衣服脱了。”我说。
他们愣了。
“头人?”“脱了。”我说,“换新的。”阿依兰打开那包袱,里头是一叠一叠的衣裳——青布的、蓝布的、灰布的,都是汉人平民常穿的那种短褂长裤。还有几顶毡帽,几根布腰带,整整齐齐地叠着。
那些人望着那些衣裳,眼睛里亮了一下,又暗了一下。
有个胆大的开口:“头人,咱们穿这个?”“对。”“那咱们的皮袍子呢?”“留着。”我说,“回部落再穿。可在西宁,在汉人的地方,咱们得穿汉人的衣裳。”他们互相看了看,没再问,开始脱那皮袍子。
河边上,二三十个狼部汉子光着膀子站着,那身子在晨光里黄黄的、黑黑的,有的胸口有疤,有的肩膀上留着熊爪的印子。他们接过那些衣裳,一件一件往身上套。
有的穿反了,有的把裤子套在了腿上才发觉那是褂子,有的系腰带系了半天系不上。阿依兰走过去,一个一个地帮他们整理,那手在他们的腰间、肩上比划着,嘴里说着“这个往这边”“那个往上提”。
我站在那儿,看着。
母亲也看着。
她没动,就靠在那柱子上,那眼睛跟着阿依兰的手,跟着阿依兰的身子,跟着阿依兰在那群男人中间走来走去。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,我说不清。
衣裳穿好了。
那些人站在那儿,穿着青布蓝布的褂子,扎着布腰带,站在那河边上,像二三十根新栽的树。虽然那脸还是狼部的脸,那眼睛还是狼部的眼睛,可那身上,已经有了点不一样的东西。
“还有一样。”我说。
我指了指自己的头发。
“把这个,剪了。”他们又愣了。
“头人,头发?”“对。剪了。”我说,“按汉人的样子,剪短,扎起来。”没人动。
我望着他们,望着他们那脸上的犹豫。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——狼部的人,从小就不剪头发,那头发是爹娘给的,是狼神给的,是命根子,剪了就是不孝,就是得罪神,就是——“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”我说,“可你们也得想想,咱们来西宁这几天,看见的那些汉人官兵,那些汉人商人,那些汉人百姓,有谁留咱们这么长的头发?”他们不说话了。
“汉人讲究的是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’,可他们不是不剪,他们是盘起来、扎起来。”我说,“咱们要想跟他们一样,要想让他们把咱们当自己人,就得先把自己收拾得跟他们差不多。”我顿了顿。
“再说了,这头发剪了还能长。可要是因为这点头发,让人家一眼就认出咱们是‘那些蛮子’,心里先存了三分防备,往后的事儿还怎么做?”他们互相看着。
然后第一个动了。
是阿固的哥哥,阿勒。他二十出头,是那群人里头最壮实的。他走到阿依兰面前,伸出手。
“借把刀。”阿依兰从腰间摸出一把小刀,递给他。
他接过,抓起自己那一把乱糟糟的长发,一刀下去,割下来好大一截。
那头发落在河边的沙地上,黑黑的,一卷一卷的。
他把刀还给阿依兰,抬起头望着我。
那头上的头发现在短了,齐着耳朵,乱蓬蓬地支棱着。
“头人,”他说,“这样行不?”我走过去,把他那头发用手拢了拢,往后脑勺那边顺了顺。
“还得扎起来。”我说,“阿依兰,有绳子没?”阿依兰从包袱里翻出几根黑布条。
我用那布条把阿勒的头发扎成一个小髻,盘在脑后。
退后一步,看了看。
“行了。”阿勒摸了摸后脑勺,那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——是那种“原来这样也行”的表情。
其他人看着,也开始动了。
一把小刀在人群里传来传去,一缕一缕的黑发落在河边的沙地上,被晨风吹着,往河里飘。那些人摸着新剪的头发,互相看着,有的笑,有的皱眉,有的在那儿照河水的倒影。
我也剪了。
阿依兰拿着刀,站在我身后。她的手轻轻的,抓起我的头发,一刀一刀地剪。那刀锋凉凉的,贴着我脖子,那头发一缕一缕地落下来,落在我的肩上,落在地上。
我抬起头,正好对上母亲的眼睛。
她还在那儿,靠着柱子,望着我,望着我身后的阿依兰。那眼睛里有光,可那光不是笑,是别的什么。
剪完了。
我站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碎发,转过身,对着那些人。
“从今天起,”我说,“咱们就是天狼卫所的人,是朝廷在册的。既然是朝廷的人,就得按朝廷的规矩办事。”我指着西宁城的方向。
“咱们要在那边设个办事处。”他们愣了。
“办事处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以后狼部跟汉人打交道,买卖也好,文书也好,拜见官府也好,都得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不能每次都像现在这样,扎个帐篷在城外。”我望着他们。
“办事处要留人。十来个弟兄,常驻西宁,看着咱们的生意,跑咱们的腿,跟汉人打交道。谁愿意?”沉默。
那些人互相看着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转——是那种“去还是不去”的犹豫。
阿勒先开口。
“头人,去了还能回部落不?”“能。”我说,“轮着来。三个月一换。”他又问:“那在那边,吃啥住啥?”“办事处管。”我说,“房子我买,粮食我出。你们就负责在那儿待着,学汉话,认汉字,熟悉汉人的规矩。往后狼部跟汉人打交道,就靠你们。”他又想了想,点点头。
“我去。”他走出来,站在我左边。
接着又走出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
最后,我左边站了八个人。
八个年轻人,穿着新衣裳,扎着新头发,站在晨光里,那脸上有紧张,也有一种“我要去闯闯”的光。
我点点头,转向阿依兰。
“办事处的事儿,你跟进。买房子,要临街的,大一点的,后院能住人。再找个师爷,要那种懂文书的、会算账的。秀才也要两个,年轻的,愿意教人念书的。”阿依兰点头。
“还有,”我说,“招募的时候,问清楚,愿意跟咱们狼部打交道的,愿意教咱们的人念书的。价钱好说,可人要踏实。”“是。”当天下午,阿依兰就带着那八个人进城了。
我在城外等着,陪着母亲,守着剩下的货物。
母亲坐在帐篷里,一直没说话。
我进去的时候,她抬起头,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话,可她不说。
我在她身边坐下。
“妈。”她没应。
我又叫了一声。
“妈。”她转过头,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的东西,我看清了。
是那种——那种怕。
不是怕狼,怕熊,怕打仗。是那种怕,是女人对女人的怕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阿依兰那女人,真能干。”又是这句话。
我望着她。
“妈,你想说什么?”她低下头,望着自己手腕上那银镯子。那镯子在帐篷里的暗光里,还是亮亮的。
她开口,那声音轻轻的。
“妈不能干。”那四个字像四块小石头。
我伸出手,想抱她。
她躲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可我看见了。
她的手攥着那银镯子,攥得紧紧的。
“妈——”“别说了。”她抬起头,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了笑——可那笑是那种“妈没事”的笑,“妈知道你忙。妈就是——就是坐在这儿,没事干,瞎想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笑,望着她那眼睛里的东西。
我想说什么,可又不知道说什么。
她就那么望着我,望着,望着,然后伸出手,摸了摸我的脸。
那手还是白白的,软软的,热热的。
“去吧,”她说,“去办你的事儿。妈在这儿等你。”我出去了。
站在帐篷外面,望着西宁城的方向,望着那天边渐渐沉下去的太阳。
心里有一团东西,堵着。
三天后,办事处的事儿办妥了。
阿依兰在西宁城南边的一条街上,买下了一个两进的院子。前面是铺面,后面是住的地方,院子里还有一口井,一棵老槐树。那师爷姓陈,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,戴着个旧毡帽,胡子花白的,可那眼睛亮得很,一看就是精明人。两个秀才是兄弟俩,姓王,大的二十四,小的二十一,都是瘦瘦的、白白的,见了人弯腰弯腰的,话不多,可那眼睛也在打量。
那八个年轻人住进了后院,每天跟着王家的兄弟念书,认字,学汉人的规矩。陈师爷坐在前头的铺子里,等着有人上门来问买卖。
我把一切安顿好,就带着母亲和阿依兰,还有剩下的货物,启程回狼部。
回去的路走得慢。
那些驮着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的牲口走得不急,我们也不急。母亲骑在马上,一路很少说话。阿依兰走在前头,招呼着那些赶牲口的年轻人,那声音脆脆的,在山谷里一响一响的。
我望着她们两个——一个在前头,一个在我身边。
心里那团东西,堵得更厉害了。
走了八天,回到狼部。
部落里的人早就在等了。
我们的队伍一出现在山口,那边就喊起来了——女人喊,孩子喊,老人喊,那声音从山脚下传过来,一浪一浪的。
我勒住马,望着那边黑压压的人群,望着那些挥着的手,那些亮亮的眼睛。
母亲在我旁边,也望着。
那眼睛里,终于有了一点笑。
进了部落,第一件事,分东西。
那些茶叶,按人头分,每家每户都有。那些丝绸,给女人分,每人一匹,自己挑颜色。那些瓷器,给每家分几个碗几个盘。那些铁器,给那些新立了帐篷的人家分锄头、镰刀、犁头。那些种子,按片分,靠近水源的那几户多分点麦种,山脚下的那几户多分点豆种。
我站在那堆货物中间,看着那些人领东西时的那张脸——那些脸黑黑的,糙糙的,可那眼睛亮得厉害,那笑从脸上溢出来,从眼睛里溢出来。
有个老妇人领了一包茶叶,捧在手里,凑到鼻子跟前闻了又闻,那眼睛里竟然有了泪。
“头人,”她说,“我三十年没喝过茶了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满脸的褶子,那混浊的眼睛里的泪。
“往后,”我说,“年年都有。”她笑了,那笑从那满脸的褶子里溢出来。
旁边有人问:“头人,这些东西,花了多少银子?”我望着他们。
“没花多少。”我说,“咱们的皮子,在那边卖了高价。”我把那数字说了。
他们愣了。
愣在那儿,张着嘴,望着我,像听错了一样。
“二十四万两?”“对。”“还有牛羊那些?”“对。”他们站在那里,互相看着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转——是那种“原来咱们的东西这么值钱”的光。
阿勒的爹,西头人,挤到我面前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脸上有两道深深的疤,是当年跟别的部落打仗时留下的。他站在我面前,那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“头人,”他说,“往后——往后咱们年年都去?”我点点头。
“年年都去。”他的嘴咧开了,那笑从那咧开的嘴里溢出来,从那两道疤里溢出来。
“好!”他一拍大腿,“好!”那天晚上,整个部落都在烧火,都在笑,都在唱。
那些茶叶被煮成一锅一锅的茶,那茶香飘得到处都是。那些丝绸被女人们披在身上,在火光里转着圈,那红的绿的蓝的在夜里一闪一闪的。那些新碗新盘被端出来,盛着肉,盛着奶,在人群里传来传去。
我坐在最大的那堆火旁边,望着这些人,望着这些笑,望着这些在火光里跳来跳去的身影。
母亲坐在我身边。
她也望着,那眼睛里有了笑,是那种真的笑。
她靠在我肩上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你真行。”我低下头,亲了亲她的头发。
阿依兰坐在火堆的另一边,跟几个女人说着什么,比划着什么。那火光在她脸上跳,把她那脸照得红红的,亮亮的。
母亲的身子僵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可她靠在我肩上的那只手,攥紧了。
第二天,阿依兰来找我。
“头人,”她说,“那个楼,修好了。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楼?”“镇守府。”她说,“你走的时候吩咐的,按汉人的样式,修一个镇守府。”我想起来了。临走的时候,我确实跟她说过,让她找人在部落里选个地方,按汉人衙门的样子,修一座镇守府。
“带我去看。”她领着我,穿过那些帐篷,走到部落东边的一块高地上。
那楼就立在那儿。
两层,木头搭的,底下是一排柱子撑着,上头是飞檐,是那种汉人房子才有的翘起来的角。那木头是新砍的,还带着树皮的边,可那样子,已经有点像模像样了。
楼下是一大间,空空的,可以议事,可以见人。楼上隔成几间,可以住人,可以存东西。
我站在那楼前,望着这狼部土地上第一座汉人样式的房子。
阿依兰站在我旁边。
“头人,”她说,“还行不?”我点点头。
“行。”她笑了,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。
“我让年轻人砍了半个月的树,又让他们照着汉人的样子搭。他们不会,我就画给他们看,一笔一笔地画。”我转过头,望着她。
她站在那儿,穿着那身蓝布的褂子,那脸在阳光下红红的,全是汗。可那眼睛亮亮的,那亮里有光——是那种“我做成了”的光。
“阿依兰,”我说,“你辛苦了。”她低下头。
“不辛苦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低下去的头,那微微抖着的睫毛。
我想说什么。
可就在这时,身后传来脚步声。
我回过头。
母亲站在不远处。
她站在那儿,望着我们——望着我,望着阿依兰,望着我们俩站在这新楼前面的样子。
那脸上没有表情。
可那眼睛里,有东西。
那天晚上,我回帐篷的时候,母亲还没睡。
她坐在那堆皮毛上,对着灯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我走进去,在她身边坐下。
她没动。
我伸出手,搂着她的肩。
她靠过来,靠在我怀里。
我们就这样坐着,坐了许久。
然后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可那轻里有东西在抖。
“儿啊——”“嗯?”“那楼,”她说,“是阿依兰修的?”“是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她真能干。”又是这句话。
我低下头,望着她的脸。
那脸上没有泪,可那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在闪。
“妈,”我说,“你听我说——”她摇摇头,不让我说下去。
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的东西,我看清了。
是怕。
是那种“妈怕你被别人抢走”的怕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妈这辈子,只有你。”那七个字像七块石头。
我望着她,望着她这张脸,这双眼睛,这个在我怀里抖着的身子。
“妈知道你忙。”她说,“妈知道你要管部落,要跟汉人打交道,要办大事。妈帮不上你。”她的声音在抖。
“可阿依兰——她能干,她会办事,她年轻,她——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我把她搂紧。
搂得紧紧的。
“妈,”我说,“你是我妈。”她在我怀里,那身子一抖一抖的。
“可你也是——”她顿了顿,那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,“你也是我老公。”那三个字像三团火。
我低下头,亲她的头发,亲她的额头,亲她的眼睛。
她抬起脸,望着我。
那脸上有泪,亮亮的,在那灯光里像水。
“妈不怕别的,”她说,“妈就怕——就怕有一天,你不再叫妈‘老婆’了。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老婆。”那两个字从嘴里出来,沉沉的,重重的。
她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老婆。”我又叫了一声。
她伸出手,摸着我的脸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热热的。
她笑了。
那笑从那满脸的泪里溢出来。
可那笑里,还是有东西。
是那种“妈还是怕”的东西。
我抱着她,抱了许久。
炉子里的火在噼噼啪啪地响,那光在我们身上一跳一跳的。
我知道,这事儿还没过去。
阿依兰的影子,还在我们中间。
往后怎么办,我不知道。
可这会儿,我抱着她,她在我怀里,这就够了。
窗外的风在吹,吹得那帐篷的布一鼓一鼓的。
远处,有狼在叫。
那是狼部的山,狼部的夜。
我搂着我的女人,听着那狼叫,望着那跳动的火光。
心里那团东西,还在堵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