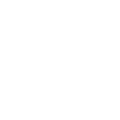22.大夏蒸汽朋克王朝?
我费了好大劲,才让玄凝冰同意我单独睡在另一间房。
她送我走到门口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舍不得,是那种“你就这么走了”的幽怨。我装作没看见,道了晚安,转身进了隔壁的厢房。
屋里点着一盏灯,昏黄黄的。我躺在那张床上,望着房梁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想到她今天说的那些话,想到她那眼神,想到她那月白的衣裙下面那熟透了的身子,翻来覆去,覆去翻来,也不知什么时候,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睡得沉。
沉得像一块石头往水里坠。
梦里头,有什么东西软软的、热热的,往我脸上蹭。一下一下的,轻轻的,像羽毛拂过,又像小兽舔舐。我想睁开眼,可眼皮沉得抬不起来,只能由着那软软热热的东西在我脸上游走——从额头到眉梢,从眉梢到脸颊,从脸颊到嘴角,最后在嘴角那里停住,压下来,软软的,湿湿的,热热的。
我想躲,可躲不开。
我想睁眼,可睁不开。
就那么迷迷糊糊的,由着那东西在我脸上作怪。
第二天一早,我是被窗外的鸟叫醒的。
阳光从窗缝里透进来,细细的几缕,落在床前的地上。我坐起来,伸了个懒腰,觉得脸上有些不对劲——黏黏的。
涩涩的。
我伸手摸了摸脸,触手之处,有些地方微微发硬,像是干涸的水渍。我下床,走到铜镜前,往里头一看——愣住了。
镜子里那张脸,左边脸颊上,好几道淡淡的红痕,像是被什么蹭过。嘴角旁边,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印子,红红的,紫紫的,分明是——吻痕。
我盯着镜子里那张脸,脑子里嗡的一下。
这——我又看了看,不止脸颊和嘴角。额头上,眉骨上,下巴上,零零散散的全是印子。有的深,有的浅,有的红,有的紫,像被人拿着印章盖了一遍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镜子里那张花花绿绿的脸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愣了好一会儿,我才反应过来。
是她。
一定是她。
我深吸一口气,胡乱擦了把脸,推开门,往隔壁走。
她的房门虚掩着。我敲了两下,没等里头应声,就推门进去。
她正坐在妆台前,对着一面铜镜梳头。换了一身衣裙,藕荷色的,料子比昨天那身还要软,贴着身子,把那熟透了的身段勾得若隐若现。那胸前鼓鼓的,把衣料撑得紧绷绷的,领口微微敞着,露出一片白腻的肌肤。那腰细细的,被一根同色的丝绦轻轻束着。那臀在凳面上压出一道圆滚滚的弧线,一直延伸到腰里,弯弯的,软软的。
她听见脚步声,转过头来。
那脸上带着刚睡醒的慵懒,眉眼弯弯的,嘴角微微翘着,像是做了什么美梦,还没从梦里头完全醒过来。
她望着我,正要开口,忽然看见我的脸,愣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可我看清了。
她那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闪了闪——是心虚,是那种“被抓包了”的慌。
然后她别过脸去,继续梳头,那声音从侧脸传来,平平的,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“起来了?洗脸了吗?一会儿要赶路,别磨蹭。”我走到她面前,站着。
她不理我,继续梳头。那梳子从发顶梳到发梢,一下一下的,慢得很,像是在故意拖时间。
我开口,那声音有点沉。
“昨晚,你进我屋了?”她的手顿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然后继续梳头。
“没进。”那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快得很,像是早就准备好了。
我弯下腰,把脸凑到她面前。
“那这是什么?”她躲了一下,没躲开,只好抬眼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扫过我的脸,扫过那些红痕和吻痕,又飞快地移开。
她的脸,红了。
那红从脸颊透出来,漫到耳根,漫到脖子,把那一片白腻的肌肤染得粉粉的。她别过脸去,不敢看我,只对着镜子,嘴里嘟囔着。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。说不定是你自己挠的。”“挠的?”我指着嘴角那块紫红的印子,“挠能挠成这样?”她不说话了。
就那么坐着,背对着我,肩膀微微绷着,像是等着我发落。
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张红透了的侧脸,望着她那微微颤动的睫毛,望着她那咬着下唇的模样,心里那团东西忽然软了一下。
她抬起头,偷偷看了我一眼,又飞快地低下头去。
那一眼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羞,是怯,是那种“我做了坏事你别凶我”的娇。
我站在那儿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也不说话。
屋里静静的,只有窗外的鸟在叫。
过了好一会儿,她开口,那声音低低的,软软的,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“你……你生气了?”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张红透了的脸,望着她那双想看我又不敢看我的眼睛,忽然觉得,气不起来了。
我叹了口气。
“没生气。”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,有一点光——是高兴,是那种“你没生气就好”的松快。
“真的?”“真的。”她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从眼睛里溢出来,从那张三十五岁的脸上溢出来,像一朵花开。她笑起来的时候,那眉眼弯弯的,那脸颊红红的,那嘴角翘翘的,整个人像是年轻了好几岁,又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。
我望着她笑,心里那团东西软得一塌糊涂。
她站起来,走到我面前,伸手,在我嘴角那块紫红的印子上轻轻摸了摸。
“疼吗?”那声音软软的,带着一点点心疼。
我摇摇头。
她点点头,把手收回去,转过身,往门口走。
“那就好。快收拾收拾,该赶路了。”我跟着她往外走。
走到门口,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赶路?坐什么车?”她回过头,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古怪,是那种“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”的奇怪。
“当然是坐火车。”火车?
我愣了一下。
火车?
这个世界,有火车?
她见我不动,又回过头来。
“愣着干什么?走啊。”我回过神来,赶紧跟上。
出了总督府,门口已经停着一辆马车。她上了车,我也跟着上去。马车动起来,车轮轧在青石板上,咕噜咕噜的响。
她坐在我对面,望着我,那眼神还是那种古怪的光。
“韩天。”“嗯?”“你刚才那表情,”她说,“像是从来没听过‘火车’这两个字似的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“我……我是没听过。”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更古怪了。
“没听过?”她说,“整个大夏朝,三岁小孩都知道火车是什么。你怎么会没听过?”我张了张嘴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望着我,望着我,望着我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果然有问题”的笃定。
“行,”她说,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马车走了小半个时辰,出了西宁城,往西郊走。远远的,我看见前头出现一座城——不,不是城。
是一座巨大的营寨,外头围着高高的围墙,墙头上插着旗子,在风里飘。围墙里面,能看见一排排的营房,整整齐齐的,像棋盘上的棋子。
可最让我震惊的,不是那些营房。
是营房后面,那一道长长的、黑黑的、像巨龙一样趴在地上的——火车。
我站在围墙门口,望着那东西,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那是一列火车。
蒸汽火车。
车头是铁的,黑漆漆的,高大得像一座小山。车头前面,一个大大的烟囱,直直地戳向天空。车头顶上,有一个圆圆的汽笛,像一只眼睛,瞪着前方。车头两侧,巨大的铁轮子,比人还高,一个挨着一个,排成两排。车轮上面,是长长的车身,一节一节的,像一条黑龙趴在地上。
可这龙,不是西洋的龙。
是中国的龙。
那车头正面,铸着一只巨大的鎏金蟠龙,龙身盘绕,龙爪张扬,龙首昂起,张着嘴,像是在咆哮。那龙的眼睛镶着两颗红宝石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像两团火。龙身四周,刻着祥云纹,云纹里嵌着各色宝石,红的是玛瑙,蓝的是青金,绿的是翡翠,在日光下熠熠生辉。
车头两侧,挂着两串铜铃,风一吹,叮叮当当地响。那响声清脆得很,像是寺庙里头的风铃,又像是宫廷里头的玉磬。
车厢也是一样。
每一节车厢都是木头做的,可那木头上,雕满了花。有缠枝莲,有如意云,有万字不到头,有福禄寿喜。雕花上涂着金漆,贴着金箔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车厢的窗户,不是西洋那种大玻璃窗,而是中国式的花窗——窗棂雕成各种花样,有冰裂纹,有万字纹,有海棠纹,每一扇都不一样。窗户上糊着明瓦,不是玻璃,是那种半透明的云母片,透光不透亮,朦朦胧胧的。
车厢与车厢之间,挂着红色的绸带,绸带上绣着龙凤呈祥、百花争艳的图案。车厢顶上,铺着琉璃瓦,黄的绿的,一片一片的,在阳光下闪着光,像是一座移动的宫殿。
我站在那儿,张着嘴,望着那列火车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这——这是火车?
这是那个世界的火车?
可那个世界的火车,哪有这样的?
这分明是一座会移动的宫殿,一条会喷火的龙,一列从神话里开出来的车。
玄凝冰站在我旁边,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看热闹,是那种“我就知道你会这样”的得意。
我转过头,望着她。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东西?”她笑了。
“火车啊。”她说,“陛下发明的。”陛下。
又是陛下。
“陛下发明的?”我的声音有点干,“什么时候?”她想了想。
“三十多年前吧。”她说,“一开始只是运煤,后来运人,再后来就修了铁路,连通了各大州府。如今大夏朝的铁路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足足有两万多里。”两万多里。
我站在那儿,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三十多年前就发明了火车。
改进更新了三十年。
如今已经有两万多里铁路。
这个绍武皇帝——他果然也是穿越者。
而且,是个比我早来三十多年的穿越者。
玄凝冰望着我,那眼神里的光,越来越古怪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你果然有问题。”我抬起头,望着她。
“这么大的事,整个大夏朝没人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?”我张了张嘴,想解释,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望着我,望着我,望着我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的事回头再跟你算账”的纵容。
“行了,”她说,“上车吧。”她拽着我的袖子,往火车走去。
那火车就在眼前,越来越近,越来越近。走近了才看清,那车头上的蟠龙,比远处看着还要大,还要精细。每一片龙鳞都刻得清清楚楚,每一根龙须都弯弯的,翘翘的,像是真的在风里飘。龙嘴里叼着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,圆圆的,润润的,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青光。
我伸手摸了摸那龙身。
凉的。
滑的。
铁的。
可那铁上面,刻着花,描着金,镶着宝,明明是冷冰冰的铁,硬生生被弄成了艺术品。
玄凝冰拽着我,走到中间一节车厢门口。那门口站着两个人,穿着青色的袍子,恭恭敬敬地弯着腰。
“将军。”“开门。”那两人推开车厢的门,露出里头的光景。
我往里一看,又愣住了。
车厢里头,不是我想象中那种硬邦邦的长条凳,也不是西洋火车那种软包的卡座。
是一间屋子。
一间中国式的屋子。
地上铺着厚厚的织锦地毯,毯子上绣着缠枝莲,莲叶田田,莲花朵朵,红的粉的白的,层层叠叠的,像是踩上去就能闻到花香。地毯上摆着一张紫檀木的矮几,矮几上放着一套青瓷茶具,那青瓷薄薄的,透透的,对着光能看见手指的影子。矮几旁边,是几个绣墩,也是紫檀木的,墩面上绣着百蝶穿花,蝴蝶大大小小,花花绿绿,像是要从墩面上飞起来。
车厢壁上,贴着云锦。那云锦是江南的贡品,一寸锦一寸金,这会儿整张整张地贴在壁上,织着如意云纹,一朵一朵的,层层叠叠的,像是把天上的云搬进了车里。云锦下面,是一排花窗。窗棂雕成冰裂纹,糊着明瓦,阳光透进来,朦朦胧胧的,把那满壁的云锦照得柔柔的,软软的。
车厢一角,摆着一张小小的香几,香几上放着一只鎏金香炉,炉子里点着香,细细的烟从炉盖的孔洞里飘出来,袅袅的,带着一股子檀香味,混着木头和织物的气息,在车厢里慢慢地散开。
另一角,是一张小小的书案,书案上放着文房四宝——笔、墨、纸、砚。那笔是湖州的,那墨是徽州的,那纸是宣州的,那砚是端州的,都是顶好的东西。书案旁边,是一个小小的书架,书架上放着几本书,线装的,蓝皮的,书脊上贴着签,写着字。
车厢尽头,是一扇屏风。屏风是紫檀木的架子,镶着绢,绢上画着山水——远山近水,小桥人家,渔舟唱晚,牧童归去。那画工精细得很,山是山,水是水,人是人,一眼看去,像是能走进去似的。
我站在车厢门口,望着里头这光景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这是火车?
这分明是一座会移动的宅子,一间会跑的屋子,一个能带着走的家。
玄凝冰拽着我走进去,顺手把门关上。
车厢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
她走到那紫檀木矮几旁边,坐下,伸手示意我坐。
我在她对面的绣墩上坐下。那绣墩软软的,坐下去整个人都陷进去一点,像是坐在云彩上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得意,是那种“怎么样,我没骗你吧”的炫耀。
“怎么样?”我点点头。
“厉害。”她笑了。
那笑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满足,是那种“你喜欢就好”的欢喜。
她伸手,从矮几底下拿出一个盒子,打开,里头是点心。桂花糕、绿豆糕、云片糕,码得整整齐齐的,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
“饿了吧?先吃点东西垫垫。等火车开起来,稳当了,再让他们上正餐。”我拿起一块桂花糕,咬了一口。那糕软软的,糯糯的,桂花的香味在嘴里散开,甜丝丝的。
她望着我吃,那眼神柔柔的。
我咽下去,抬起头,望着她。
“从这儿到皇都,要多久?”她笑了笑。
“三天。”三天?
我愣了一下。
西宁到北京,放在我那个世界,坐火车也得一天一夜。这儿的火车,居然只要三天?
她见我愣着,又笑了。
“陛下发明的这东西,快得很。比骑马快,比马车快,比什么都快。从西宁到新皇都北京,三千多里地,三天就到。”新皇都。
北京。
我望着她,心里那团东西又翻了一下。
北京。
新皇都。
也就是说,这个世界的京城,已经不是长安了,是北京。
绍武皇帝迁了都。
把京城从长安迁到了北京。
我坐在那儿,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窗外,忽然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——呜——那声音又高又亮,像一头巨兽在咆哮。紧接着,车身轻轻一震,又一震,又一震。
然后,动了。
车轮轧在铁轨上,发出有节奏的响声——咣当,咣当,咣当。那声音稳稳的,沉沉的,像一首古老的歌谣,在车厢里回荡。
窗外的景物,开始往后退。
先是那围墙,那营房,那站台。然后是田野,是村庄,是山,是水。一切都在往后跑,越跑越快,越跑越远。
我坐在那儿,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三天。
三天之后,我就能见到那个绍武皇帝了。
那个可能也是穿越者的皇帝。
那个比我早来三十多年的穿越者。
玄凝冰坐在我对面,望着我,那眼神柔柔的。阳光从花窗里透进来,朦朦胧胧的,照在她脸上,把她那张三十五岁的脸照得软软的,暖暖的。
她开口,那声音轻轻的。
“韩天。”我转过头,望着她。
“嗯?”她望着我,那嘴角翘起来,弯弯的。
“你脸上那些印子,”她说,“真的不是我弄的。”我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她也笑了。
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开,载着我们,往那新皇都,往那北京城,往那不知是福是祸的前路,一路奔去。
火车开起来,稳得很。
咣当咣当的声音,不急不慢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窗外的景物往后飞驰,田野、村庄、山川、河流,一片一片的,像翻书似的,翻过去就不回头。
我坐在绣墩上,望着窗外,心里那团东西还没完全静下来。
玄凝冰坐在我对面,也不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那眼神柔柔的,像一汪水,时不时在我脸上那些印子上扫过,嘴角就忍不住翘一翘。
我知道她在笑什么,懒得理她,只顾着看窗外。
过了没多久,车厢门被轻轻敲响。
“进来。”门推开,进来两个穿着青衣的丫鬟。一个手里端着托盘,托盘上放着几碟点心和一壶茶;另一个捧着一叠纸,叠得整整齐齐的,放在矮几上。
“将军,茶点备好了。这是今天的报纸。”报纸?
我心里一动。
那丫鬟把托盘放下,把茶壶摆好,把茶盏斟满,又弯了弯腰,退了出去。门轻轻关上,车厢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。
玄凝冰伸手,从那叠纸里拿起一张,递给我。
“看看吧。”我接过来,低头一看——那是一张报纸。
真正的报纸。
对开大小,印刷清晰,上头密密麻麻的都是字。最上头是四个大字:大夏时报。字下面是一行小字:绍武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,第四千七百二十一期。
四千七百二十一期。
我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。
绍武三十四年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就算一周三期,三十四年下来,也差不多是这个数。
也就是说,这份报纸,已经办了三十多年。
我低下头,看那报纸上的内容。
头版头条,是一则消息:陇右节度使奏报,西陲各部归心,边患渐平,陛下嘉奖诸将。下面是一行小字,写着陇右节度副使玄凝冰的名字。
我抬起头,看了她一眼。
她正端着茶盏,慢慢地喝着,那眼睛却从茶盏边上瞄着我,等着看我的反应。
我没说话,继续往下看。
第二版,是各地的消息。江南丰收,两湖水利,京师新闻,边关战报。第三版,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——商号开张,货物行情,寻人启事,还有几则广告。第四版,是文章。有论农桑的,有谈水利的,有讲边事的,还有一首诗。
我翻来覆去地看,看了好一会儿。
报纸。
印刷。
铅字。
排版。
广告。
这东西,放在我那个世界,再寻常不过。可放在这个世界——我抬起头,望着玄凝冰。
“这报纸,”我说,“也是陛下发明的?”她点点头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骄傲,是那种“那是自然”的自豪。
“三十多年前就有了。一开始只是京城里有,后来各大州府都有了。如今整个大夏朝,每天卖出去的报纸,有几十万份。”几十万份。
我坐在那儿,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报纸。
印刷术。
发行网络。
每天几十万份。
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识字的人多。意味着信息传播得快。意味着朝廷能把自己的声音,送到千家万户。
这个绍武皇帝——他不仅是个穿越者。
他还是个有手段的穿越者。
他知道怎么改造这个世界,怎么建设这个世界,怎么掌控这个世界。
我坐在那儿,望着手里那张报纸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然后我抬起头,望着她。
“凝冰。”“嗯?”“我还有一件事想问。”她放下茶盏,望着我。
“问。”我压低声音,那声音轻轻的,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。
“火枪和大炮,”我说,“是不是也已经有了?”她的脸色,变了。
那脸上的笑,一点一点地收起来。那眼睛里柔柔的光,一点一点地冷下去。她望着我,那眼神像两把刀,在我脸上刮着。
车厢里静静的,只有车轮咣当咣当的声音,一下一下的,像是我的心跳。
她开口,那声音冷得很。
“韩天,这种帝国最高机密,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刚才还笑意盈盈、如今却冷得像冰的脸,心里那团东西反倒静下来了。
果然。
火枪和大炮,也有了。
这个绍武皇帝,比我以为的还要厉害。
她见我不说话,那眼神更冷了。
“说。”我望着她。
“凝冰,”我说,“如果我说,我和陛下,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——你信吗?”她愣住了。
那脸上的冷,一点一点地裂开。那眼睛里的刀,一点一点地钝下去。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震惊,是不信,是那种“你在说什么”的茫然。
“你说什么?”我望着她。
“我说,我和陛下,也许来自同一个地方。”她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可没说出来。
就那么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过了许久,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那声音干干的,涩涩的,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“你……你到底是什么人?”我望着她。
“我叫韩天,”我说,“江南苏州府吴县人,当年跟着父亲去波斯做生意,被蛮人掠了去,后来在狼部立足,被朝廷册封为镇守使——这些都是真的。”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,等着。
我顿了顿。
“可在那之前,”我说,“我在另一个世界,活了二十多年。”她的眼睛,动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可我看清了。
我继续说:“那个世界,也有火车,也有报纸,也有火枪大炮。那个世界,比这里先进得多,也复杂得多。我在那个世界,是个普通人,过普通的日子。后来不知怎么的,一觉醒来,就到了这里。”她听着,那眼神复杂得很。
“你是说——”“我是说,”我望着她,“陛下,也许和我一样。他也是从那个世界来的。”她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开口,那声音轻轻的,像是怕惊着什么似的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?”我心里那团东西,猛地跳了一下。
她知道。
她知道陛下是穿越者。
我望着她。
“你早就知道?”她点点头。
那动作轻轻的,可那轻里有一种沉。
“我母亲告诉我的。”她说,“当年陛下起兵的时候,身边只有几个人。我母亲,我姨母,还有皇后娘娘。她们是陛下最亲近的人,也是最早知道陛下秘密的人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陛下亲口告诉她们,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他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,那个地方有火车,有报纸,有火枪大炮,还有好多好多她们想都想不到的东西。”我听着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“你母亲信了?”她点点头。
“一开始不信。后来见陛下拿出那些东西——那些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就信了。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新的东西——是好奇,是打量,是那种“原来你也是”的光。
“你真的是……”我点点头。
“是。”她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不是刚才那种温柔的笑,也不是比武场上那种欣赏的笑。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——有点懵,有点愣,有点像是听见了什么她这辈子都没想过的事。
“原来如此。”她说,“原来如此。”她说着,低下头,望着矮几上那盏茶,望着那茶里自己的倒影。
过了好一会儿,她抬起头,又望着我。
“你刚才说的那些——火枪,大炮——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我想了想。
“猜的。”我说,“既然有火车,有报纸,那火枪大炮应该也不远了。这些东西,在那个世界,是连在一起的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你猜对了。”她顿了顿,那声音压得更低了。
“火枪和大炮,确实有了。是陛下亲自带着人研制的。如今禁军里,已经有了火枪营。大炮还少,只有京城和几个要紧的地方有。这是帝国最高机密,知道的人,不超过一百个。”我听着,心里那团东西又翻了一下。
火枪营。
大炮。
这个绍武皇帝,果然不简单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认真,是那种“这事不能乱说”的警告。
“韩天,这事你知道就行,别往外说。这是陛下的命根子,也是大夏朝的命根子。要是传出去,让北边的蛮子知道了,让西边的那些部落知道了,让他们有了防备,那可就坏了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又软了下来。
“你刚才说,你和陛下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那地方,到底是什么样的?”我想了想。
“很复杂。”我说,“说不清。”她点点头,没再问。
就那么坐着,望着我。
我坐在那儿,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窗外的天,蓝蓝的,有几朵白云,慢慢地飘着。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,绿的黄的,像一块巨大的织锦铺在地上。远处有山,隐隐约约的,像水墨画里的影子。
火车咣当咣当地开着,载着我们,往那新皇都奔去。
过了许久,她开口,那声音轻轻的。
“韩天。”我转过头,望着她。
“嗯?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光。
“到了京城,见了陛下,你打算怎么办?”我想了想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,“看陛下的意思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也对。”她顿了顿,那嘴角微微翘起来,像是在笑。
“不过,有件事我倒是知道了。”“什么事?”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,亮亮的,软软的。
“你果然是嫌弃我老。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我没有——”“你有。”她打断我,那笑从眼睛里溢出来,“你那个世界的人,肯定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姑娘。我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女人,你当然看不上。”我张了张嘴,想解释,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望着我那张着嘴愣住的样子,那笑更浓了。
“行了,”她说,“逗你玩的。”她伸手,拿起茶壶,给我斟了一杯茶。那动作轻轻的,柔柔的,像是在做一件很要紧的事。
她把茶盏推到我面前。
“喝茶。”我端起茶盏,抿了一口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柔柔的。
“韩天。”“嗯?”“不管你是哪儿来的,”她说,“你是我看上的人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这事,改不了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三十五岁的脸,望着这双柔柔的眼睛,望着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女人。
心里那团东西,软得一塌糊涂。
窗外,火车还在咣当咣当地开着。
载着我们,往那新皇都,往那北京城,往那不知是福是祸的前路,一路奔去。
三天。
整整三天,我坐在这列龙形火车里,穿过山川,穿过河谷,穿过一座又一座我从未见过的城市。
每到一个地方,火车会停一停。有时候停得久,有时候只停片刻。可不管停多久,总会有新的厨师上来,端着新的托盘,摆上新的菜肴。
第一天中午,火车停在一个叫兰州的地方。上来的厨师端着一盘烤羊排,那羊排烤得外焦里嫩,滋滋地冒着油,撒着一层红红的辣椒面和孜然,香得人直流口水。配菜是一碟糖蒜,一碟黄瓜条,还有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。
我吃着羊排,望着窗外。兰州的车站不大,可站台上人来人往,有穿长衫的,有穿短打的,还有几个穿着皮袍子、戴着皮帽子的胡商,牵着骆驼,等着装货。
第二天傍晚,火车过了太原。上来的厨师换了一拨,端上来的菜也换了样。莜面栲栳栳,一碗一笼的,蒸得软软的,蘸着羊肉臊子吃,香得很。还有一碗刀削面,面片薄薄的,滑滑的,汤里飘着香菜和葱花,喝一口,暖到心里。
我吃着面,望着窗外。太原的车站比兰州的大,站台上停着好几列火车,有的拉货,有的拉人。远处能看见城墙的影子,灰灰的,长长的,在暮色里像一条沉睡的龙。
第三天中午,火车进了河北地界。上来的厨师端着一盘驴肉火烧,火烧烤得酥酥的,夹着切得薄薄的驴肉,咬一口,满嘴都是香。还有一碗小米粥,稠稠的,糯糯的,配着一碟腌萝卜条,清淡爽口。
我吃着火烧,望着窗外。河北的地势平坦,一望无际的田野,麦子绿油油的,一片连着一片,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绿毯。偶尔能看见村庄,灰墙青瓦,炊烟袅袅,有孩子在田埂上跑,有老人在门口晒太阳。
玄凝冰坐在我对面,也吃着,喝着,时不时抬眼望我一下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满足,是那种“看你吃得香我就高兴”的欢喜。
三天下来,我吃了兰州羊排、太原刀削面、河北驴肉火烧,还有一路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小吃。每一道菜都精致,都地道,都像是把当地的山水风土装进了盘子里。
第三天傍晚,火车开始减速。
窗外,天色渐渐暗下来,暮色四合,远远的天边还剩一线橘红。我坐在窗边,望着外头,等着看那传说中的新皇都——北京。
应该是什么样的?
我想象过很多次。
也许是高高的城墙,灰砖青瓦,绵延不绝,像一条巨龙趴在地上。也许是四合院,小桥流水,胡同纵横,有老人在树下下棋,有孩子在巷子里跑。也许是宫殿,金顶红墙,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像梦里才有的仙境。
我想着想着,火车又拐了一道弯。
然后——我看见了。
那不是城墙。
那是——烟囱。
无数的烟囱。
高高低低,粗粗细细,一根一根戳向天空,像一片黑色的森林。烟囱里冒着烟,有的黑,有的白,有的黄,一股一股地往天上蹿,把傍晚的天空染得灰蒙蒙的。那烟在半空里散开,聚成一团团一簇簇,像一大片脏兮兮的云,压在城市上头。
烟囱下面,是房子。
不是我想象中那种灰墙青瓦的四合院。
是高楼。
真正的高楼。
七八层的,十来层的,甚至更高的,一栋一栋挤在一起,密密麻麻的,像一片石头森林。可这些楼,不是我那个世界的玻璃大楼——它们不是光滑的,不是整洁的,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现代感。
它们是中式的。
楼顶是飞檐翘角,挂着风铃,在暮色里叮叮当当地响。楼身上雕着花——有缠枝莲,有如意云,有万字不到头,有福禄寿喜。雕花涂着金漆,贴着金箔,在烟囱里冒出的火光里一闪一闪的。
可那些雕梁画栋之间,伸出来的——是管道。
铁的管道,粗的细的,一根一根从楼里伸出来,像藤蔓一样爬满墙壁,又像血管一样盘根错节。有的管道往上走,有的往下走,有的横着穿过街道,连接到另一栋楼上。管道上冒着热气,滋滋地响,在暮色里蒸腾出一团团白雾。
管道之间,是齿轮。
巨大的齿轮,有的比人还高,有的比房子还大,镶在楼身上,卡在管道中间,一个咬着一个,慢慢地转着。齿轮转动的时候,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,那声音沉沉的,闷闷的,像是这座城市的呼吸。齿轮的边缘镶着铜,在暮色里泛着黄黄的光,一转一转的,像无数只眼睛在眨。
更高的地方,是塔。
那些塔比楼还高,一座一座戳向天空,塔尖是尖尖的,弯弯的,像寺庙里的塔刹。可塔身上,也爬满了管道,镶满了齿轮。塔的顶上,有巨大的风扇,在风里慢慢地转着。风扇的叶片是木头的,漆着红漆,一转一转的,像巨大的风车。
风扇转动的时候,会带动塔里的什么东西,发出嗡嗡的声音。那声音从高处传下来,混着齿轮的咔嚓声,混着管道的滋滋声,混着烟囱的轰鸣声,混成一片巨大的、沉沉的、永不停息的喧响。
我趴在车窗上,张着嘴,望着外头那片光景,整个人都傻了。
这——这是什么?
这是我那个世界的北京?
这分明是——蒸汽朋克。
中式蒸汽朋克。
烟囱冒着烟,齿轮转着,管道爬满墙壁,风扇在塔顶慢慢地转。可那些烟囱上雕着龙,那些齿轮上镶着金,那些管道旁边挂着红灯笼,那些塔顶上盖着琉璃瓦。
烟囱里冒出来的烟,在暮色里被灯笼一照,变成一团一团红红黄黄的光。那些光在半空里飘着,散着,把整座城市罩在一层朦朦胧胧的纱里。
街道上,有马车。
马车还是主流。一匹一匹的马,拉着车,在街上慢慢地走。车轮轧在青石板上,咕噜咕噜地响。车夫坐在车辕上,甩着鞭子,吆喝着让行人让路。
可偶尔,有另一种东西从马车旁边驶过。
那是——蒸汽车。
铁的,黑黑的,比马车大一些,也高一些。车头有一个小小的烟囱,突突地冒着白烟。车底下是铁轮子,比马车的轮子粗,也比马车的轮子宽。轮子转动的时候,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,和那些大齿轮的声音一样,只是小一些,轻一些。
蒸汽车从马车旁边驶过,马车夫会侧着头看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羡慕,是好奇,是那种“迟早我也要弄一辆”的光。
我望着窗外那片光景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三天前,我看见火车的时候,已经震惊过一次。
可那火车,好歹是个单独的物件。是一个东西。
眼前这个——是一座城。
一整座城。
一座用烟囱、管道、齿轮、风扇堆起来的城。一座把中式雕梁画栋和西洋蒸汽机器揉在一起的城。一座活着、响着、冒着烟、转着齿轮的城。
我趴在车窗上,望着那座城越来越近,越来越近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玄凝冰坐在我对面,望着我这副样子,那嘴角翘得高高的。
她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我,望着我笑。
火车慢慢减速,穿过那片烟囱和齿轮的森林,往站台驶去。
又过了片刻,火车终于停了。
我往窗外一看,愣住了。
这是站台。
可这站台,和我一路上见过的那些站台完全不一样。
大。
太大了。
几十条铁轨,上百条铁轨,密密麻麻地排开,像一片铁的森林。每一条铁轨上都停着火车,有的在等人,有的在卸货,有的在冒着白烟准备出发。那些火车有长有短,有黑有绿,车头上的蟠龙有金有银,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。
铁轨之间,是站台。
一条一条的站台,又长又宽,上面挤满了人。有穿长衫的,有穿短打的,有背着包袱的,有拎着箱子的,有抱着孩子的,有牵着老人的。有人在跑,有人在喊,有人在挥手告别,有人抱在一起哭。
站台顶上,是一个巨大的顶棚。
那顶棚是玻璃的,一块一块拼起来的,像一个大大的盖子,罩在整座车站上头。顶棚下面,挂着一排一排的灯笼,红的黄的,照得整个车站亮堂堂的。
可最让我震惊的,是那顶棚尽头,那一面巨大的——钟。
那钟比房子还大,圆圆的,亮亮的,镶在顶棚的墙上。钟面是白的,数字是黑的,两根针一长一短,慢慢地走着。钟下面,是一块巨大的牌子,黑底白字,上面写满了字——车次,时间,目的地。那牌子一格一格的,像翻页似的,时不时翻动一下,换一换上面的字。
牌子翻动的时候,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。
那响声一响,站台上的人就会抬头看,然后有人跑起来,有人喊起来,有人往某条铁轨那边挤。
广播。
有广播。
那声音从头顶上传来,是女人的声音,字正腔圆的,一遍一遍地播着车次和时间。那声音在巨大的站厅里回荡着,嗡嗡的,混着人群的喧哗,混着火车的汽笛,混成一团巨大的、混乱的、嘈杂的声响。
可这声响——熟悉。
太熟悉了。
这是我那个世界的火车站。
是那种我坐过无数次的、挤满了人的、乱糟糟的火车站。
我趴在车窗上,望着外头那光景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有震惊,有恍惚,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,还有一种更说不清的——想哭的冲动。
三天。
三天的火车,三天的震惊,三天的恍惚。
从蒸汽火车到报纸,从火枪大炮到这座蒸汽之城。
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可这一刻,听见那广播的声音,看见那巨大的时钟和那翻动的时刻牌,我忽然觉得——这个世界,比我想象的,要复杂得多。
那个绍武皇帝,比我想象的,要厉害得多。
玄凝冰站起来,走到我身边,也往外头看了看。
“到了。”她说,“下车吧。”我回过神来,跟着她站起来。
刚走到车门口,车门就被从外面打开了。
门外,站着两排人。
一边是穿青袍的官员,五六个,规规矩矩地站着,弯着腰。另一边是穿灰军装的兵,也站成一排,手里端着——枪。
火枪。
长长的,黑黑的,枪口上插着刺刀,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。
那些兵站得笔直,望着前方,一动不动,像一排铁铸的雕像。
官员里头,走出一个胖胖的中年人,穿着青色的官袍,戴着乌纱帽,满脸堆笑地弯下腰。
“下官京城西站知事,恭迎玄将军。”玄凝冰点点头,没说话,只是拽着我的袖子,走下车门。
那些官员让开路,那些兵也侧过身,把我们和站台上那些挤挤挨挨的乘客隔开。有一个兵在前面带路,其余的跟在后面,把我们护在中间,往站台旁边走。
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站台上,那些人还在挤,还在跑,还在喊。他们望着我们这一队人,望着那些端着枪的兵,望着被护在中间的我和玄凝冰,那眼神里有好奇,有羡慕,还有那种“不敢靠近”的畏。
一个小孩被母亲抱在怀里,伸着脖子往这边看,那眼睛亮亮的,望着我们这一行人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我转过头,跟着那带路的兵,往前走。
走到站台尽头,有一个向下的楼梯。楼梯口站着两个兵,也是端着枪的,看见我们过来,啪地并腿敬礼。
我们走下楼梯。
楼梯很长,弯弯曲曲的,像是要往地底下去。墙壁上点着灯,一盏一盏的,照得亮堂堂的。楼梯走完,是一条通道,也是地下。通道两边也是墙,墙上也点着灯。脚下是石板,铺得平平的,走起来没有声音。
走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,通道到了尽头。又是一道楼梯,往上走。走完楼梯,推开一扇门——外头,是一个巨大的广场。
站前广场。
广场上,人更多。有推着车的小贩,有牵着马的脚夫,有等着拉客的车夫,有送人接人的百姓。人声鼎沸,乱糟糟的,比站台上还热闹。
广场边上,停着许多马车。有普通的,有豪华的,有敞篷的,有带篷的。马车夫们站在车旁,扯着嗓子喊:“朝阳门!”“崇文门!”“宣武门!”一声一声的,像是在比谁的嗓门大。
偶尔,有一辆蒸汽车从马车旁边驶过,咔嚓咔嚓地响着,冒着白烟。那蒸汽车比马车快,也比马车稳,从人群里穿过去,人们纷纷让路,望着那车的眼神里有羡慕,也有敬畏。
那带路的兵走到一辆马车前,停下。
那马车,比广场上其他的马车都大,都豪华。
车身是紫檀木的,雕满了花。有龙凤呈祥,有百花争艳,有福禄寿喜,有万字不到头。雕花上涂着金漆,贴着金箔,在暮色里闪闪发光。车顶是琉璃瓦的,黄的绿的,一片一片的,像一座小小的宫殿。车窗是花窗,糊着明瓦,朦朦胧胧的。车门前挂着一盏灯笼,红红的,亮亮的,照得车前的石板都泛着红光。
车前,是四匹马。
四匹白马,高大得很,比寻常的马高出半个头。马身上披着锦缎,锦缎上绣着云纹,马头上戴着红缨,红缨在风里一颤一颤的。
马车夫站在车旁,穿着青色的袍子,戴着同色的帽子,恭恭敬敬地弯着腰。
那带路的兵转过身,冲玄凝冰抱了抱拳。
“将军,请上车。”玄凝冰点点头,拽着我的袖子,往马车走。
我跟着她,上了车。
车厢里,比我想象的还要豪华。
地上铺着厚厚的织锦地毯,毯子上绣着缠枝莲,红的粉的白的,层层叠叠的。车厢壁上贴着云锦,织着如意云纹,一朵一朵的,像是把天上的云搬进了车里。车厢一角摆着一张小小的香几,香几上放着鎏金香炉,炉子里点着香,细细的烟从炉盖的孔洞里飘出来,袅袅的。
车窗边,是两张软榻。
软榻上铺着锦垫,锦垫上绣着百蝶穿花,花花绿绿的,像是要从榻上飞起来。
玄凝冰在一张软榻上坐下,伸手拍了拍旁边的另一张。
“坐。”我在她旁边坐下。
车门关上,马车动起来。
车轮轧在青石板上,咕噜咕噜地响。那响声和火车的不一样,软软的,绵绵的,像是催眠曲。
我坐在那儿,望着窗外。
马车穿过广场,穿过人群,穿过那些喊着的马车夫和让路的百姓,往广场外头驶去。
广场外头,是一条大街。
街上灯火通明。
两边是店铺,一家挨着一家。有卖布的,有卖粮的,有卖茶的,有卖杂货的。店铺门口挂着灯笼,红的黄的,照得整条街亮堂堂的。街上有行人,有马车,偶尔有蒸汽车咔嚓咔嚓地驶过。
远处,那些烟囱还在冒着烟。那些齿轮还在转着。那些风扇还在慢慢地摇着。
夜色里,那些烟囱、齿轮、风扇、飞檐翘角,混在一起,朦朦胧胧的,像一幅画,又像一场梦。
我望着窗外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三天。
三天前,我还在西宁。
三天后,我到了这里。
这座烟囱和齿轮之城,这座雕梁画栋和蒸汽管道之城,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。
我转过头,望着玄凝冰。
她也望着我,那眼神柔柔的,亮亮的,在车厢里的灯光下一闪一闪的。
她开口,那声音轻轻的。
“韩天。”“嗯?”“欢迎来到北京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三十五岁的脸,望着这双柔柔的眼睛,望着这个坐在我旁边的女人。
窗外,马车还在往前走。
载着我们,往那不知在何处的住处,往那未知的明天,往那座烟囱和齿轮之城深处,一路驶去。
与此同时,在数千里之外的高原上。
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,冷得刺骨。太阳已经落下去,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暗红,像一道还没干透的血痕。那血痕映在雪山上,把那些终年不化的白雪染成淡淡的粉色,又慢慢变成灰色,最后沉入夜色里。
金川部的营地坐落在两座山之间的谷地中。一条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,河水是雪山上下来的,冷得刺骨,在暮色里泛着灰白的光。河边扎着几百顶帐篷,有黑的有白的,密密麻麻的,像一群趴在地上喘息的野兽。
最大的那顶帐篷里,点着几盏油灯。
灯芯噼啪地响着,火光一跳一跳的,把帐篷里那些人的影子投在毡壁上,忽长忽短,忽大忽小,像一群不安分的鬼魂。
甲洛跪在地上。
他是金川部的头人,在这片高原上,他的名字能止小儿夜啼。可此刻,他跪在冰冷的毡子上,低着头,望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连喘气都不敢大声。
他的身后,跪着几个头人。有老有少,有胖有瘦,可此刻都一样——低着头,弯着腰,像一群被宰杀前的老羊。
他们面前,站着一个男人。
那男人穿着陇西军的军服——灰蓝色的袍子,外头罩着皮甲,腰间挂着一把刀。那刀没有出鞘,可甲洛知道,那刀只要出鞘,就会有人死。
男人的脸被油灯的光照着,一半亮一半暗。那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冷冷的,淡淡的,像是在看一群蝼蚁。
他开口,那声音不高不低,可那不高不低里,有一种让人骨头缝里发冷的东西。
“大人指示。”
甲洛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。
“你们几个,去灭了狼部。”
甲洛猛地抬起头。
灭了狼部?
他望着那军官,那眼睛里全是震惊。那震惊里,有恐惧,有不解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——愤怒?
“大人——”
军官抬起手,打断他。
那动作轻轻的,可那轻轻里,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。
甲洛张了张嘴,又把嘴闭上了。
军官继续说:“特别是要处理了狼部头人的那几个婆娘。明白吗?”
甲洛跪在那儿,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狼部头人。
韩天。
那个据说从狼群里杀出来的男人。那个亲手杀了三个头人、把他们的头挂在杆子上的疯子。那个在西宁城打败了所有高手的怪物。
灭了他?
灭了他的部族?
还要处理了他的婆娘?
甲洛觉得自己的嗓子眼里有什么东西堵着,咽不下去,也吐不出来。
他跪在那儿,犹豫了许久,才开口。那声音干干的,涩涩的,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。
“大人,按大夏律,这可是违法的。”
军官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他。
甲洛被那目光盯着,后背上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起来。可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下去。
“驻藏大臣那边……怎么办?他要是知道了,我们金川部可就……”
他的话没说完,就被身后一阵轻轻的咳嗽声打断了。
甲洛回头看了一眼。
是他的长子,洛桑。
洛桑跪在几个头人后面,低着头,看不清表情。可那一声咳嗽,甲洛听懂了。
别说了。
甲洛转过头,又望着那军官。
军官还是那副冷冷的表情,像是在看一场戏。
甲洛咬了咬牙,又说:“而且,狼部也是大族。他们有六万多人,能打的少说也有七八千。我们金川部……”
他的话又没说完。
军官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从那冷冷的脸上溢出来,像一朵冰山上开出的花。可那花里,没有暖,只有更深的冷。
“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。”
军官说。那声音轻轻的,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甲洛愣住了。
“大人——”
“耽误了玄大人的事,”军官打断他,那声音还是轻轻的,“你们都得死。”
那几个字落在帐篷里,像几块石头砸进水里。甲洛身后的头人们,身子都微微颤了一下。有一个年轻的,甚至忍不住往后退了退,膝盖在毡子上蹭出一声闷响。
甲洛跪在那儿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都得死。
玄大人。
玄凝冰。
那个女人。
那个据说比男人还狠的女人。
甲洛想起那些关于她的传说——说她十二岁就上过战场,说她亲手杀过十七个蛮族勇士,说她当年跟着陛下平乱的时候,一把刀杀穿了整条街。
那样的女人,要灭狼部?
要杀韩天的婆娘?
甲洛想不通。
可他不敢问。
他只是跪在那儿,低着头,望着地上那几根草茎。那草茎被他的膝盖压着,弯弯的,像是要断了。
军官望着他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满意,是那种“这就对了”的光。
他开口,那声音还是轻轻的。
“至于狼部的几万人,这不是问题。”
甲洛抬起头,望着他。
军官说:“过几天,你们在山谷里会发现一些东西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一些武器。”
甲洛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武器?
军官继续说:“洛桑会教你们如何使用的。”
甲洛愣住了。
洛桑?
他猛地转过头,望向身后。
洛桑正慢慢地站起来。
火光映在他脸上,把那年轻的脸照得明明暗暗的。那脸上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甲洛从未见过的光。那光是亮的,是热的,是那种“我终于等到这一天”的兴奋。
洛桑走到军官面前,站定。
然后他弯下腰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军官点点头。
洛桑直起身,转过身,望着甲洛,望着那几个跪在地上的头人。
他开口,那声音年轻得很,可那年轻里,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是骄傲,是得意,是那种“你们以后都得听我的”的笃定。
“父亲,各位叔伯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会教会族人用那些武器的。”
甲洛跪在那儿,望着自己的长子,望着这张他从小看到大的脸,望着那双他以为他全都了解的眼睛。
那眼睛里,有他从未见过的东西。
是野心。
是那种“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”的野心。
甲洛忽然觉得,眼前的这个人,不是他儿子。
是一个陌生人。
帐篷里静静的,只有油灯的灯芯在噼啪地响。
军官站在那儿,望着这一幕,那嘴角微微翘着,像是在笑。
他开口,那声音从高处落下来,像一道旨意。
“事情办妥了,玄大人不会亏待你们的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办砸了——”
他没往下说。
可那没说出来的话,比说了的还重。
甲洛跪在那儿,望着洛桑,望着那张年轻的脸,望着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。
他忽然想起韩天。
想起那个据说从狼群里杀出来的男人。
想起那个亲手杀了三个头人的疯子。
想起那个在西宁城打败了所有高手的怪物。
如果那怪物知道他要去灭狼部,要去杀他的婆娘——
甲洛打了个寒颤。
洛桑走过来,弯下腰,伸手扶他。
“父亲,起来吧。地上凉。”
那声音轻轻的,柔柔的,像是在哄一个孩子。
甲洛望着他,望着这张笑着的脸,忽然觉得,这笑比那军官的冷脸,还要让人害怕。
帐篷外,风还在吹。
那风从雪山上下来,冷得刺骨,吹过帐篷,吹过河谷,吹过那些黑黑白白的帐篷,往东边吹去。
往狼部的方向吹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