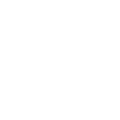20.大夏玄家
那天晚上,我一直没睡着。
怀里,母亲睡得沉沉的,呼吸匀匀的,胸口一起一伏。我望着帐篷顶那黑黑的影子,望着那从缝隙里漏进来的星光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天亮的时候,我下了决心。
母亲醒过来,睁开眼,望着我。那眼睛刚睡醒,还带着一点迷糊,可那迷糊里,有那种“妈知道你一夜没睡”的光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你想了一夜?”
我点点头。
她坐起来,靠在那些皮毛上,望着我。
“想清楚了?”
我又点点头。
“妈,”我说,“既然已经决定收留丹珠,那跟金川部的冲突,就躲不掉了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
“甲洛那个人,”我说,“心狠手辣。他敢抢自己侄女的地盘,就敢往东边伸爪子。咱们狼部这半年发展得快,可快是快,底子还薄。真打起来——”
我顿了顿。
“真打起来,未必输。可就算赢了,也是惨赢。死几百人,伤几千人,那些新开的田,那些新修的房,那些刚走上正道的日子,都得毁。”
她的眼睛动了动。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
我望着她。
“我要去汉地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“去汉地?”
“对。”我说,“去西宁,去凉州,如果可能,去长安,去京城。”
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了问号。
“去干什么?”
“去要个名分。”我说,“一个更大的名分。”
我顿了顿,把那几个字说出来。
“青海护边使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
“狼部镇守使,”我说,“管的是狼部的事。可青海护边使,管的是整个青海地面的事儿。有了这个名分,我就能调动更多的兵,能跟陇西军平起平坐,能在朝廷那边挂上号。甲洛再横,也不敢轻易动朝廷命官。那些收了礼的官员,也不敢明着帮他。”
她听着,那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。
“能要到吗?”
我想了想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,“可总得试试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试试好。”
她伸出手,摸着我的脸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热热的。
“儿啊,”她说,“妈有个事要跟你说。”
“你说。”
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柔柔的。
“妈不跟你去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为什么?”
她低下头,望着自己的肚子。那肚子还是平平的,可她知道,我也知道,那里面有个东西在长。
“妈这个样子,”她说,“走不了那么远的路。再说——”
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妈得留在这儿。”
我望着她,等着她说下去。
“丹珠刚来,”她说,“阿依兰在这儿。妈得看着她们。”
我心里一动。
“妈——”
“别说了。”她摇摇头,“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放心,妈不会跟她们闹。妈会把她们照顾好,会让她们好好的。”
她顿了顿,那嘴角动了动,像是想笑。
“等妈把孩子生下来,等她们两个都跟妈一条心了,等你从汉地回来——”
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亮亮的。
“那时候,咱们的家,就真正稳了。”
我望着她,望着这个女人,我的妈,我的老婆,我孩子的娘。
心里那团东西,堵得更厉害了。可那堵里,有一种热——是那种“有她真好”的热。
我低下头,吻她。
她回应我,那嘴唇软软的,热热的,带着早晨的味道。
我们吻了许久。
松开的时候,她喘着气,那胸一起一伏的。
她望着我,那眼睛亮亮的。
“去吧。”她说,“妈等你回来。”
三天后,我出发了。
那天早上,天刚蒙蒙亮,狼部的人都出来了。
山坡上,河谷边,那些新修的房屋前面,站满了人。男人,女人,老人,孩子,黑压压的一片,从镇守府门口一直排到山口那边。
我站在那二十多个护卫前面,望着这些人。
阿勒站在我旁边,牵着我的马。那马是黑色的,高头大马,是上次从西宁买回来的,养了半年,养得膘肥体壮,皮毛亮亮的,在晨光里泛着光。
母亲站在台阶上。
她穿着那身青布褂子,头发挽着,肚子还是看不太出来。可她站在那儿,那身子比以前更稳了,那眼睛比以前更深了。
阿依兰站在她右边。
她穿着那身蓝布褂子,头发也挽着,脸上薄薄地敷了粉,那眉眼还是那样秀气。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话,可她没说出来。
丹珠站在她左边。
她来了三天,洗了澡,换了衣裳,吃了热饭,睡了好觉,那脸色好多了。她穿着阿依兰给她找的衣裳,青布的,合身的,头发也梳起来了,在脑后挽了个髻。她站在那儿,那眼睛也望着我,那黑黑的眼珠子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会记住你的恩”的东西。
三个女人,站在那儿,站在晨光里。
我望着她们。
她们也望着我。
母亲先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可那轻里有沉。
“路上小心。”
我点点头。
阿依兰开口。
“头人,商队那边的事,我会管好。丹珠妹妹我会照顾。老夫人这边——你放心。”
我又点点头。
丹珠开口。
那声音还有点哑,可那哑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会报答”的东西。
“大人,一路平安。”
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黑黑的眼睛。
“别叫我大人。”我说,“叫大哥就行。”
她愣了一下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过。然后她低下头。
“大哥。”
那两个字让我心里一热。
我转过身,翻身上马。
那马动了动蹄子,打了个响鼻。
我勒住缰绳,最后望了一眼那三个女人,望了一眼那些黑压压的人群,望了一眼这座新修的镇守府,望着这片正在一点点变样的山谷。
然后我挥了挥手。
“走。”
二十多匹马动了。
马蹄声踏破了清晨的寂静,在山谷里响着,像一阵闷雷。
我骑在马上,望着前方那渐渐亮起来的天,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路。
身后,那些声音还在——那些送行的喊声,那些孩子的哭声,那些马嘶声,那些风吹过梯田的声音。
我没回头。
可我知道,她们还在那儿站着,望着我,望着我这越来越远的背影。
妈。
阿依兰。
丹珠。
三个女人。
我走了,把她们留在一起。
我不知道这三个月会发生什么。不知道她们会不会真的像妈说的那样,好好相处。不知道阿依兰会不会甘心被制衡,不知道丹珠会不会真的站在妈那边,不知道妈能不能真的管住她们。
我不知道。
可我知道,我必须走。
为了狼部,为了这个家,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,为了这三个女人——我得去汉地,去要那个名分。
青海护边使。
有了这个,我才能护住她们,护住这片地方,护住这些正在一点点变好的日子。
马跑起来了。
风在耳边呼呼地响。
那山,那水,那梯田,那些人,一点一点地往后退,越来越小,越来越远。
我抬起头,望着前方。
前方是天边那一道亮光,是太阳正要升起的地方。
是西宁。
是汉地。
是那更大更远的世界。
我骑着马,往那光里奔去。
心里那团东西,还在堵着。可那堵里,有了一种新的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会回来的”的劲儿。
我会回来的。
带着那个名分回来。
带着朝廷的文书回来。
带着能让她们安心的东西回来。
妈,等我。
阿依兰,等我。
丹珠,也等我。
我会回来的。
马跑得更快了。
那二十多骑,像一阵风,刮过那清晨的山谷,刮过那刚醒来的草原,刮过那一片片绿油油的梯田,往东边去了。
太阳终于跳出来了。
那光照在我身上,暖暖的,亮亮的。
我眯起眼睛,望着那光。
心里,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那是——希望。
四天后,西宁城的城墙出现在眼前。
还是那座土黄色的城,还是那高高的箭楼,还是那些在风里飘的旗子。可这回看着,跟上次不一样了。上次来,是带着几千张皮毛,几百头牛羊,心里头全是买卖,全是银钱,全是那些数字。这回,心里头装的是别的东西——是那个名分,是那个“青海护边使”,是那三个站在晨光里送我的女人。
我们在城外勒住马。
阿勒靠过来,问:“头人,先找地方落脚?”我摇摇头。
“先去找周哨官。”周哨官叫周德胜,陇西军前营哨官,管着西宁城外的巡查。这半年,我没少给他送东西——茶叶,皮毛,宝石,还有两匹好马。他也帮我不少忙——部族里那几个年轻人,就是他收进军营的,如今干得不错,有俩已经当了伍长。
他是我们在西宁最靠得住的人。
我们在城东的校场找到了他。
他正坐在校场边上的一个棚子里,面前摆着碗茶,手里拿着个本子在看。听见马蹄声,他抬起头,眯着眼往这边望。等看清是我,那脸上露出笑来。
“韩兄弟!”韩兄弟。
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。韩天。
韩是国姓,是皇帝老儿的姓。在这汉人的地方,姓这个,听着就有分量。再说了,我本来就是江南人,姓韩也不算冒充。
我跳下马,走过去。
他站起来,抱了抱拳。
我回了个礼。
他打量着我,那眼睛里亮亮的。
“半年不见,韩兄弟气色更好了。”我笑了笑。
“周哨官也是。”他摆摆手,招呼我坐下,又让人上茶。
我坐下来,阿勒他们站在棚子外面等着。
他端起茶碗,抿了一口,望着我。
“这回怎么亲自来了?商队的事儿,不是都交给那个女官了?”我摇摇头。
“这回不是买卖的事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“那是?”我往四周看了看。棚子外面,有几个兵在远处走动,听不见我们说话。
我压低声音。
“周哨官,我想求个事。”他的眼睛动了动。
“说。”“我想见更大的官。”他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了问号。
“更大的官?多大?”我想了想。
“能管整个青海地面的那种。”他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那眼睛里的光在动,在转,在想着什么。
然后他开口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想往上走?”我点点头。
他又端起茶碗,喝了一口,放下。
“你跟哥哥说实话,”他说,“你到底想要什么?”我望着他,望着这个帮了我半年的人。
“青海护边使。”那五个字说出来,他的眼睛睁大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可他听见了。
他放下茶碗,往后靠了靠,那脸上的表情复杂起来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这个心,不小啊。”我没说话。
他望着我,望着,望着,然后叹了口气。
“你知道朝廷对高原上那些部落是个什么态度不?”我摇摇头。
“你说。”他伸出一根手指。
“一,按时纳税。该交的皮毛,该交的牛羊,一文不能少。”又伸出一根。
“二,服兵役。朝廷要人,你们得出人。巡逻,打仗,平叛,都得去。”第三根手指。
“三,别的,朝廷一概不管。”他望着我。
“你们部落谁当头,谁死了,谁抢了谁,谁被赶跑了——朝廷不闻不问。只要你们不造反,不拦着商道,不劫朝廷的物资,爱怎么打怎么打,爱怎么闹怎么闹。”我听着,心里那团东西沉了一下。
“那——那我这个镇守使——”“那是个名头。”他说,“让你们跟汉人做买卖方便,让你们有个身份,让你们觉得自己是朝廷的人了。可真出了事,朝廷会不会管?难说。”我坐在那儿,望着他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翻去。
他望着我这表情,又叹了口气。
“韩兄弟,不是哥哥泼你冷水。实在是——朝廷的事儿,没那么简单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望着我。
“可你还是想试试?”我点点头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开口,那声音压低了些。
“韩兄弟,你运气好。”我心里一动。
“怎么说?”他往四周看了看,凑近了些。
“过几天,有个人要来西宁。”“谁?”“陇右节度副使,玄凝冰。”玄凝冰。
陇右节度副使。
那是个大官。比驻藏大臣小不了多少,管着陇右这一大片地方的兵马钱粮。
“他来干什么?”“巡查。”周哨官说,“每年都来。看看边防,看看军备,看看那些部落安分不安分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你要是能见到他,把你想说的话说给他听——兴许,还有机会。”我坐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跳了一下。
玄凝冰。
这是个机会。
可我怎么才能见到他?见了又怎么说?他凭什么听我一个小小的狼部镇守使说话?
我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,嘴里随口问了一句。
“节度使大人姓玄——和当朝玄悦贵妃,可是同门?”周哨官愣了一下,那脸上的表情变了。
他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知道的还不少”的光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知道玄家?”我摇摇头。
“就知道个名字。”他往四周看了看,又往棚子外面望了望,确认没人靠近。然后他压低声音,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“玄家,那是当朝第一等的人家。”我竖起耳朵。
“玄家一门,”他说,“出过三凤。”三凤。
那是什么?
他伸出一根手指。
“老大,玄素。当年是皇后娘娘身边的高级军官,带过兵,打过仗。后来跟了陛下,当了中央军校的校长。那可是教将军的地方。”又伸出一根。
“老二,玄悦——就是现在的玄贵妃。她早年是陛下的侍卫,跟陛下出生入死,立下过赫赫战功。后来当了禁军统领,管着京城的安全。”他顿了顿,那声音压得更低了。
“听说当年,为了护着陛下,她跟她大姐玄素拔刀对峙过。”我心里一动。
姐妹拔刀?
“跟皇后娘娘那边,也一直不对付。”他说,“可陛下信她,信得不得了。她生的皇子,燕王韩珺,如今官拜大将军王,管着北边的兵。当年朝鲜那边叛乱,燕王半个月就平了,那是有玄将军当年的风采。”半个月平朝鲜。
那得是多大的本事。
我望着他,等他继续说。
他伸出第三根手指。
“老三,玄凤。当年是近卫军副统领。陛下安排她去看着那个虞朝皇帝——就是后来被废了的虞昭。后来,也是她帮着陛下,把虞昭废了。”他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深得很。
“这么说吧,韩兄弟。陛下能坐上这个位置,玄家那三位,出了大力。”我坐在那儿,脑子里把这些话一一收进来,一一摆好。
玄素。玄悦。玄凤。
皇后那边的,贵妃那边的,废帝那边的。
三姐妹,三个方向,三条路。
可她们都姓玄,都是玄家的人。
那这个玄凝冰——我开口。
“那这位玄凝冰大人——”周哨官点点头。
“是老三玄凤的小女儿。”我愣在那儿。
玄凤的女儿。
那位帮着陛下废了虞朝的玄凤,的女儿。
来西宁了。
周哨官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光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?”我摇摇头。
他笑了。
那笑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真是运气来了”的东西。
“玄家的人,”他说,“跟别的官不一样。”“怎么不一样?”“他们自己就是打仗出身。玄素打过仗,玄悦打过仗,玄凤也打过仗。她们手底下的人,也打过仗。她们知道什么叫真本事,什么叫假把式。她们不像那些文官,坐在衙门里看折子听汇报——她们见过血。”他望着我。
“你要是能让她看见你的本事,看见你真能管住那些部落,真能稳住那片地方——她说不定,真会帮你。”我心里那团东西跳得更厉害了。
“可她凭什么见我一个狼部头人?”周哨官想了想。
“这个嘛——”他沉吟了一下,“得等机会。”他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你这几天别走。就住在西宁,等消息。我帮你留意着,什么时候玄大人到了,什么时候有机会见面,我告诉你。”我站起来,冲他抱了抱拳。
“周哨官,大恩不言谢。”他摆摆手。
“别谢太早。能不能成,还得看你的造化。”我点点头,转身要走。
他又叫住我。
“韩兄弟。”我回过头。
他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哥哥再嘱咐你一句”的光。
“玄家的人,”他说,“眼睛里不揉沙子。你要见她,就得说实话。别装,别吹,别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。就老老实实说你是谁,你干了什么,你想要什么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她们这种人,听了一辈子假话。你给她们真话,她们反倒会高看你一眼。”我望着他,心里那团东西热了一下。
“记住了。”我出了棚子,翻身上马。
阿勒他们围过来。
“头人,去哪儿?”我望着西宁城里那一片片房屋,那一条条街道,那远处隐约可见的衙门屋顶。
“进城。”我说,“找个地方住下。”“住多久?”我想了想。
“住到该见的人见到为止。”马蹄声响起来。
我们往城里去了。
身后,那校场越来越远。周哨官还站在棚子边上,望着我们,那身影在夕阳里越来越小。
我心里那团东西,还在跳。
玄凝冰。
玄凤的女儿。
陇右节度副使。
她要来西宁了。
这是个机会。
可这机会能不能抓住,能抓住多少,抓住之后会怎么样——我不知道。
可我知道,我得试试。
为了狼部那六七万人。
为了那三个在等我的女人。
为了我肚子里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。
我得试试,随即,我把那袋子放在桌上。
牛皮袋子,鼓鼓囊囊的,往那木头案子上一放,发出沉甸甸的一声闷响。
周德胜低头看了一眼,又抬起头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动了动。
“韩兄弟,这是——”我没说话,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。解开布包,里头是两颗宝石,一颗红的,一颗蓝的,在那棚子里昏昏的光线里,一闪一闪的。
我把它们放在那袋子旁边。
红的那颗,像一滴凝固的血。蓝的那颗,像一汪从天上剪下来的天。
周德胜的眼睛落在那些宝石上,停了一会儿,又移开,望着我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那声音沉了沉,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我望着他。
“周兄,”我说,“这半年,你帮了我多少,我心里有数。”他摆摆手,要说话。
我不让他说。
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”我说,“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。可这回的事儿不一样。”他望着我,等着我说下去。
“这回要官,”我说,“不是为了我自己。”我顿了顿,让那几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一转。
“是为了我狼部那几万百姓。”他的眼睛动了动。
我接着说:“你是知道的,我是汉人。江南人,苏州府吴县的。我那个部族,几百号人里头,有汉人,有羌人,有藏人,还有几户回回。可我这个头人,是汉人。我心里向着谁,向着哪儿,我清楚。”他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
“可金川部那些头人,”我说,“甲洛那一伙子,他们是藏人,是羌人,是蛮族。”我把那两个字咬得重了些。
“蛮族。”他的眉头动了动。
“他们跟我不一样。”我说,“他们见利忘义。谁给的钱多,他们跟谁走。谁的势力大,他们听谁的。什么朝廷,什么王化,什么大义——他们不认那些。”我往前探了探身子,望着他的眼睛。
“周兄,你想过没有——要是甲洛真当上了金川镇守使,他会干什么?”他没说话。
“他会往东边伸爪子。”我说,“他会打我狼部的主意。他会抢我的牧场,占我的盐井,拦我的商队。我打不打?打,两败俱伤。不打,我狼部几万人吃什么喝什么?”我顿了顿。
“我打了,朝廷管不管?不管。我是狼部镇守使,他是金川镇守使,我们两个打,那是蛮族内斗,朝廷不闻不问。可打着打着,商道断了,税收少了,那些羌人藏人看着朝廷不管,心就野了——到时候,乱的就不是两个部落,是整个青海。”周德胜听着,那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。
我往后靠了靠,把那口气缓一缓。
“可要是朝廷信我,”我说,“让我当这个青海护边使——我能把那些事情,都办好。”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怎么说?”“我会在高原上推广王化。”我说,“让那些羌人藏人学汉话,认汉字,读汉人的书,懂汉人的规矩。让他们的孩子进儒学,考秀才,当朝廷的官。让他们的头人按朝廷的法子办事,纳税,服兵役,巡逻边境,打击叛乱。”我望着他。
“到时候,朝廷省了军费——不用年年派兵来平叛,不用月月拨银子来安抚。百姓有了和平——那些羌人藏人不用今天被这个部落抢,明天被那个部落杀。羌藏各部也有了保障——有朝廷撑腰,有商路可走,有日子可过。”我把最后那几个字说出来。
“多好。”周德胜坐在那儿,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深得很。
他看了我许久。
然后他叹了口气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这些话,要是说给别人听,人家当你在吹牛。可说给我听——”他顿了顿。
“我信。”我心里那团东西热了一下。
他低下头,望着桌上那袋银子,那两颗宝石。然后他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这东西,我不能收。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周兄——”他摆摆手。
“你别急,听我说。”他说,“这半年,你给我的东西够多了。茶叶,皮毛,那两匹马——我记着呢。帮你,是应该的。你要是再给我这个,那就是见外了。”我望着他,心里那团东西翻了一下。
“可这事儿,得打点。”我说,“上面那些人——”他又摆摆手。
“上面那些人,”他说,“我替你打点。”他伸出手,把那袋银子和那两颗宝石推回来。
“这些,你收着。等我需要的时候,我再跟你开口。”我望着他,望着这个坐在我对面的人,这个帮了我半年的哨官,这个愿意替我去打点上面的人。
心里那团东西,热得厉害。
“周兄——”他笑了。
“别周兄周兄的了。”他说,“叫我德胜就行。”我也笑了。
“德胜。”他点点头,端起茶碗,喝了一口。放下茶碗的时候,那眼睛往我这边瞄了瞄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刚才说,你有东西要给玄大人?”我心里一动。
“有。”我从怀里掏出那个东西。
那是一个表。
机械表。
不是这世上的东西。
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,随身带着的几样东西之一。我一直没舍得用,一直贴身藏着,藏在最贴肉的地方,藏在那些皮袍子里头,藏在那些没人能摸到的地方。
我把它放在桌上。
周德胜低下头,看着它。
那表是圆的,银色的壳子,亮亮的,在那昏昏的光线里泛着冷冷的光。表盘上是白的,有黑色的数字,有三根细细的指针,一根时针,一根分针,一根秒针——那秒针还在走,一下一下的,跳着走。
周德胜的眼睛落在那个跳着的秒针上,落在那些数字上,落在那银色的壳子上。
他看了许久。
然后他抬起头,望着我。那眼睛里,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——是惊,是奇,是那种“这是什么东西”的茫然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那声音有点干,“这是——什么?”我望着他。
“表。”“表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看时辰的。”我指了指那三根针。
“这根短的,是时针。走一格,是一个时辰。这根长的,是分针。走一圈,是一个时辰。这根最细的,是秒针。它走一下,就是一呼吸的功夫。”他望着那根还在跳的秒针,望着它一下一下地跳,一下一下地走。
那眼睛里的光,深得看不见底。
“这东西,”他说,“哪儿来的?”我想了想。
“祖上传下来的。”我说,“我爷爷的爷爷,从西洋那边带回来的。传了几辈子,传到我手里。”他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那表。
我接着说:“这东西,我从来没舍得用。一直藏着,藏在最贴身的地方。因为它不是钱能买来的——这世上,就这么一块。”我顿了顿。
“我想把它,送给玄将军。”周德胜抬起头,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,有了一种新的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真是下了血本”的敬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这东西——”我打断他。
“我知道这东西值钱。”我说,“可再值钱的东西,也是死物。我要是能当上青海护边使,能护住我那几万人,能让这片地方太太平平的——那这东西,就花得值。”他望着我,望着,望着。
然后他把那表拿起来,对着光看。
那表在他手心里,亮亮的,那秒针还在跳,一下一下的,像一颗小小的心。
他看了许久。
放下。
抬起头,望着我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那声音沉沉的,“你放心。这东西,我一定替你送到玄大人手里。你的话,我也一定替你传到。”我站起来,冲他抱了抱拳。
“德胜,拜托了。”他也站起来,回了个礼。
“等着。”那天晚上,我躺在西宁城一家客栈的床上,望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,怎么也睡不着。
脑子里翻来覆去的,全是那些事——那袋银子,那两颗宝石,那块表,周德胜望着那块表时的眼神,他说“等着”时那脸上的表情。
那块表,跟了我十几年。
从穿越过来的第一天起,它就贴在我胸口,贴着我的肉。夜里睡觉的时候,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,摸着它才能睡着。白天赶路的时候,我把它藏在最贴身的地方,怕丢了,怕被人偷了,怕这世上唯一能证明我来处的东西没了。
现在,它不在了。
它在我怀里贴了十几年,贴得那银色的壳子都暖了,贴得那表盘上都有了我的体温。现在它不在了,我胸口那块地方,空落落的,像少了什么。
可我知道,这东西,花得值。
玄凝冰。
玄凤的女儿。
陇右节度副使。
她要是见了这块表,会怎么想?
会收下吗?
会帮我吗?
会让我当那个青海护边使吗?
我不知道。
可我知道,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
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白白的,冷冷的。
我翻了个身,闭上眼睛。
眼前浮起三个人的脸。
妈挺着肚子,站在晨光里,望着我。
阿依兰站在她右边,那眼睛里有话。
丹珠站在她左边,那黑黑的眼珠子里,有那种“我会记住你的恩”的东西。
她们在等我。
等我把那个名分带回去。
等我把那能护住她们的东西带回去。
等我回去。
我闭上眼睛,让那些脸在黑暗里慢慢淡去。
窗外,远远的,有更夫在敲梆子。
咚。咚。咚。
三更了。
我数着那梆子声,一下一下的,像那块表上的秒针。
一下,一下,一下。
跳着走。
走着走。
往那不知道的前头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