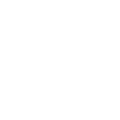第八章
很远很远的地方,好像有哭声。飘渺,像隔着一层雾。
我被人死死抱着。嘴里的东西又酸又粘。费力地掀开一点沉重的眼皮。是姐姐模糊的轮廓。对不起…终究还是连累你了……为什么就差那么一点点……为什么今天会回来……
她抱着我的手臂抖得厉害,一直不停地重复着:“小川醒醒……小川醒醒……”
想说:姐姐,我好困,让我睡一会儿……却张不开嘴。
我微微睁开的眼睛又合上了。
“小川!别睡!姐姐在!别睡啊小川!!” 她用力撑开我眼皮,“看着姐姐!姐姐知道你醒了!” 泪水砸在我脸上。
姐姐,就让我睡会儿……一会儿就好……
车上,她不停地呼唤我的名字,拍我的脸颊。不知过了多久,那些声音终于停了。
再睁眼时。夕阳正沿着手背上的输液管,慢慢往上爬。也把姐姐趴在床沿沉睡的身影,镀上一层暖融融的橘色。
她一只手紧攥着我插着针的手。手背上,粘着干涸发黑的点,大概是我呕吐时她慌乱擦拭留下的。
目光落在她挽起袖口露出的那片淤青。是扶我上救护车撞的吗?对不起……
用能动的那只手,轻轻拂开她鬓角碎发,小心翼翼地别到耳后。她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了几下,醒了。眼睛红肿得厉害。
“小川……” 她声音沙哑。我手在她手心微弱地回握了一下,算是回应。
很久,她才想起什么,拿起棉签蘸了水,小心擦拭我干裂的嘴唇。“渴吗?” 问完,又像刚反应过来,“医生说只能喝粥……姐姐去买?”
她连着问,我才点了下头。
“嗯,姐姐这就去。” 她不舍地松开我的手,走到门口,又忍不住回头深深看了一眼,“一定……等姐姐回来。”
塑料饭盒揭开,夕阳裹着米香升腾。她舀起一勺粥,唇瓣轻轻碰了碰勺沿试温,才小心喂到我嘴边。
我要了湿巾。她翻包,哗啦作响——缴费单、揉皱的会议纸,还有那张染着呕吐物的三行遗书,皱巴巴的,显然被她捏过。
“姐姐…别哭……”我用湿巾轻轻擦过她憔悴的脸颊,抹掉蜿蜒的泪痕。
“姐姐不哭,” 她抓住我的手,贴在自己脸上,“小川好好的……姐姐就不哭。” 窗外,暮色正吞噬最后一缕霞光。监护仪幽绿的光投在墙上,映出我们依偎的影子。
“姐姐……我想过些天转学回县城。你能……再帮我一次吗?” 声音几乎要哭出来。怕她像那晚一样斥责我,虽然知道她此刻是清醒的。
“这么急?” 她低下头,睫毛湿漉漉的。
“我不属于这儿。”
“好。姐姐正好也回。”
“你也回?”
“嗯。妈妈说老房顶漏雨……得回去修修。”
夜里,让她挤上窄小的病床。她侧身躺下。深夜隔壁床鼾声如雷,她突然带着压抑的哭腔梦呓:“别…别离开妈妈……”
伸手想去安抚她的肩膀,却摸到一手汗。不想吵醒她梦见女儿。可惜,那似乎是个令人心碎的噩梦。
她惊醒过来,睫毛仍是湿漉漉的,猛地紧紧抱住我:“小川……”
没敢问那是个怎样的梦。也没敢问,她决定回去……真的只是为了修房顶?还是在这座城市,没什么值得留念了?还是因为我……
这一切混乱的漩涡,都因我的闯入而搅动得更深。
厨房里飘出久违的油烟香气,混合着饭菜的暖意。她的身影好几次在门框边犹豫地探出来,又悄悄地缩回去。我慢慢蹲在门框边,静静看着她忙碌的背影。她又一次回头,手里还捏着半根蔫头耷脑的芹菜梗。
“帮姐姐剥几瓣蒜?” 她愣了一下,随即把一个小搪瓷碗轻轻塞进我手里。
铁锅里油花滋滋响。她翻炒着青菜:“公司最近在研究个新东西……关于嗅觉记忆的。知道吗?” 热气熏得她眯起眼,“就像……闻到樟脑丸那股味儿,就能想起老家那掉了漆的木箱……闻到下雨前那股闷闷的泥土腥气,就能想起夏天夜里憋着不下雨的闷热……”
“还有闻着刺鼻的酒气,就想起厕所地上那个陌生的姐姐……” 我心里默念。
清蒸鱼冒着袅袅白汽被端上桌,姐姐说等等班主任。门铃响了。老师坐在我对面,筷子在米饭里戳出一个小坑:“转学证明,下周就能拿了。”
姐姐夹起鱼肚子上最肥嫩雪白的那块肉,稳稳放进老师碗里,声音温和:“麻烦您了,老师。”
“老师……帮我跟贾艳说声谢谢。” 谢什么呢?说不清楚。大概是,谢谢她曾经给予我的那份纯粹而明亮的善意。而且,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门口,她们压低的说话声像细碎的雨点,听不分明,隐约有个“对不起”。
拎回来一大塑料袋药盒。饭气还没在胃里落稳,就得吞下苦涩的药片。没十分钟,眼皮就变得·沉重。挪回房间,栽进床里。姐姐倚在门框边,手抠着门板上的反锁扣。
再睁眼,天色已近黄昏。下午六点。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挤上来的,就安静地躺在我旁边。
“小川醒了?” 她侧过脸,“身上都有味儿了,姐姐给你洗洗好吗?”
“嗯。” 我点了下头。
浴室里,热水哗哗冲着。她手指沾着滑腻的香皂泡,在我脊背、胳膊上搓洗。皮肤底下传来一阵阵陌生的酸麻感,像通了微弱的电流。这突如其来的、久违的亲近,反而让我有些无措的僵硬。
傍晚,我说想出去透口气。她没拦:“记得饭点回来。”
一个人慢慢晃到河边的木栈道。夕阳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,像通往远方的、模糊的线。
找了个没人的石头凳子坐下。透着一丝傍晚的凉意。
能捡回这条烂命,大概得感谢那安眠药——里头有催吐成分,硬是把胃里那些致命的酒精和抗生素给顶了出来。也没被秽物呛死。兴许……是姐姐当时手快,把我嘴里那堆脏东西掏干净了。
脑子里又翻出刚到这那晚,她抱着我讲的故事:那个被钉在轮椅上的人——史铁生。
二十一岁,一场高烧,两条腿成了摆设。他也想过死。后来,摇着那架吱呀响的轮椅,钻进地坛那片野草荒树里。看虫子打架,看蚂蚁搬家,日复一日地思索人活着的意义。
他母亲,总偷偷跟在后头护着。等他第一篇作品终于变成铅字时,母亲早已不在人世。成了他心里头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深洞。
我学不来他。我没有他那样的坚韧。也没有人会那样无声地守在我身后,我也不需要。更找不到一片能容我喘息、思考的“地坛”。
这河边的石凳,坐久了硌得慌。风,也渐渐凉了。
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*****